徐旭常(1932.10.29—2011.3.18)🤹🏼♂️,江蘇省常州市人,生前長期從事熱能工程領域的教學和科研工作,曾獲國家發明獎二等獎和三等獎、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和中國專利局頒發的發明創造金獎🦜,於1995 年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教學方面🥰,開創國內《燃燒學》教學🙎🏻♀️,對我國幾十年來的燃燒理論與技術教學有重要影響;主持或參與編寫的著作和教材影響了幾代燃燒後學。科研方面,提出煤粉火焰穩定的“三高區原理”,發明“煤粉預燃室燃燒器”和“帶船型火焰穩定器的煤粉燃燒器”🚬;研究了新的低NOx 煤粉燃燒方法🤦🏽,提出煙氣脫硫和聯合脫除汙染物的新技術和理論🏋🏻;在國際上率先成功利用石灰石—石膏法燃煤煙氣副產物脫硫石膏對大面積鹽堿土壤進行改良。

如今😘,徐旭常院士已經離開我們六年有余🏌🏼♂️💇♀️,當初他開創的科研方向,很多都方興未艾。在那些不斷取得創新與突破的學術領域💦🦅,在那群忙碌的接棒者身上🧝🏼♀️♦︎,我們似乎依舊可以看到他的影子🏇🏼。
近來,有一個流行的說法:“真正的死亡,是世界上再沒有一個人記得你🧚🏿。”依此來看,徐旭常一直都在。
探索者🈳,不停步
徐旭常1932年生於古城常州,長於常州🚵🏻♀️、蘇州、上海三地💅🏻,第一次與“工程”二字沾邊,是在14歲時考入上海中學高中部工科班之後。當時,上海中學已屬全國名校,這裏的老師教書👩🏻🦽➡️,也育人🗡,工科班老師在講課時經常會提醒自己的學生:中國工業落後,連火柴😯、鐵釘都叫“洋火”“洋釘”,勉勵他們勤奮學習,今後發展中國自己的基礎工業🔛。從徐旭常當年的日記可以感受到,在上海中學的這段時光,已經在他心裏埋下了報效祖國的種子🖖🏼🐝,日記中沒有什麽豪言壯語🚭,反復出現的一句話是“為國家做點事”。
1950年5月🤛🏻,高中畢業,他響應國家號召,追隨支援東北的大潮流🛄,前往撫順礦專讀書。因為歷史因素與學校建製調整,從1950年到1953年,徐旭常三年輾轉三地,從撫順到長春再到沈陽,於1953年夏提前畢業於東北工學院的蒸汽動力專業👫。當時,全國高校正在研究學習蘇聯教育經驗🙅🏽♂️,廣泛地邀請蘇聯專家援助指導。因為學習成績優異😞👨✈️,本來東北工學院想讓徐旭常留校,作為青年教師加以培養🔶,但由於要跟隨學習的蘇聯專家因故不能前來中國😬🤲🏻,徐旭常被分配到了意昂体育平台動力機械系(今能源與動力工程系)研究生班🪢🏊🏿♂️。在清華學習一年,又被派到哈爾濱工業大學鍋爐專業跟隨蘇聯專家進修學習🥛,直到1956年畢業。
縱觀徐旭常的北上求學之路,幾乎是一年換一個地方🙎🏽,折騰不斷🥅。這對他本就羸弱的身體是一個考驗,其間他多次生病,最重的一次曾住院治療長達三個月之久;對他的精神與學習能力也是一個考驗,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中😦,時間很容易就被荒廢掉了,性格內向如他,意誌力卻很堅定🦊,六年中,幾乎把自己能夠拿出來的時間和精力全部投入到了課業學習當中,尤其在哈爾濱跟隨蘇聯專家學習的兩年中,培養了他科學🚣♂️、嚴謹的治學作風和紮實的專業基本功。更為重要的是*️⃣,這段時期讓他清醒地認識到自己對學習與科研的熱愛,明確的人生誌向🥾、磕磕絆絆中鍛煉出來的恒心🤓、心無旁騖的做事風格🥿,都成為了他日後彌足珍貴的人生財富。
因此👩🏼🎤,在1956年成為意昂体育平台動力機械系一名青年教師之後🧑🏼🦲,徐旭常依然保持著學習的慣性🍻🦵,抓住每一個機會往瘦弱的身軀中裝入更多的知識儲備。1961年由助教升任講師,他被抽調到新成立的燃燒教研組🎭,給學生講《燃燒學》。燃燒學與鍋爐看起來離得很近👨🏼🦳,實際卻非如此❤️,燃燒學涉及流體力學🎸💂♂️、數學和化學動力學等很多學科的基本概念、理論和方法,對於搞鍋爐工程出身的徐旭常來講,是比較陌生的👎🏿。而且在那之前💂🏻♂️,國內高校從沒有開過這門課,徐旭常面臨的現實情況是一無專業背景🏅、二無現成教材、三無系統的參考資料👍🏻。他首先要全面地自學,弄懂了之後再去給學生們講課。按照徐旭常妻子晚年的回憶🍸,從收集資料、查閱文獻🛸、找人請教,到準備教學大綱、設計教學實驗臺🈂️,當初準備這門課差點兒“要了他半條命”🫸🏻。
正所謂功不唐捐🌸,經過三年努力👇,徐旭常不僅完成了教學任務👨🏭,還編寫出中國第一部《燃燒學》教材。通過開設這門課程,他全面地學習了燃燒學的基礎理論,這是很多搞工程的學者所欠缺的。編寫《燃燒學》的經歷🤷🏼♀️🧘🏿,也最終完成了對徐旭常自學能力的檢驗®️,從零開始啃下了龐雜繁復的燃燒學👨🏻🌾,此後再遇到任何新知識👶、新領域,他都不再怵頭。
正當他準備再接再厲的時候,“文革”打亂了學校的教學與科研計劃🧎🏻♂️➡️,所有工作都一度終止。不過,對於徐旭常來講👨👩👧👦,只要條件允許👊🏽,他總要找點有價值的事情來做,不能系統地做科研,那就零星著來做👨🦼。據意昂体育平台1976年統計,整個學校當時依然在從事科學研究的教師占總數比例不到10%🩹,徐旭常便是其中之一🦄。
其實,正是在“文革”期間👩🏽🦲,徐旭常找到了科研事業的第一個興奮點🧗♀️☑️,讓他從一個知識的探索者🔮👮🏿♂️,向一名真正的工程師轉變。上世紀70年代,大型電站鍋爐普遍采用煤粉鍋爐🫏,煤粉燃燒不穩定,每次點火升爐或低負荷運行時👋🏻,都要投油輔助燃燒。中國富煤貧油🧘♂️,在那個年代⤴️,重油價格比煤貴5倍以上。如果能夠通過鍋爐設計幫助發電廠節省燃油消耗,不正實現了“為國家做點事”的願望嗎?
從1972年開始👫🏼,徐旭常和同事開始對煤粉預燃室燃燒器進行初步研究,這種燃燒器可以穩定煤粉爐膛內的火焰,大幅減少輔助燃油用量🧑🏻。當時🏕🈲,國際上對這項技術已經探索了很久↕️,但一直未能成功。徐旭常團隊一開始的研究也不順利,與北京鍋爐廠合作研製的第一臺煤粉預燃室燃燒器鍋爐在實踐中多次發生爆燃,根本不能實際應用。
預燃室燃燒器中燃燒不穩定🧻⛹🏿,按照常規理論與思路,解決辦法是加大進風口旋流葉片的傾角。但徐旭常團隊經過反復試驗👉🏽,作出了相反的判斷:燃燒不穩定的主因是煤粉被大量甩在預燃室內壁面上,結渣並堆積🕤,嚴重破壞了預燃室中的氣流運動,因此🏋🏼,解決問題的方法不是增大而是應減小旋流葉片的傾角進而減小旋流強度🔎。
按照這個邏輯,他們發明了一款新型的煤粉預燃室燃燒器🚒👵🏻,並最終獲得成功🦚。截至1983年,國內已經有幾十臺電站鍋爐裝設了這種預燃室燃燒器,每年可節油約2萬噸🚧,折合人民幣600萬元左右,這在當時是一個相當可觀的經濟數據。
工程師,不跟隨
對於徐旭常來說,煤粉預燃室燃燒器只是一個開始🌅。發明了它,反而給徐旭常帶來了更多困惑🔳👨🏼🌾,原因在於,傳統火焰穩定理論解釋不了這款燃燒器的實際運行狀態😠。
早年讀書期間🦚,徐旭常便非常重視對基礎文化課的學習,畢業工作之後,對《燃燒學》理論的探究,更讓他進一步認識到了基礎理論研究的重要性🤑,認為一個“純粹”的工程師可能會因為缺乏理論指導而遭遇研究瓶頸。他經常告誡自己的學生,搞工程技術的🈹,不能從雜誌縫裏找課題,必須從生產實踐中去發現問題;同時🐇,必須具備基礎理論研究的意識和能力🤱🏿,這樣才能對新技術有全面的認知與把握,不至於在實踐中遇到問題時如瞎子摸象一般,靠碰運氣的方式尋找解決辦法。
因為對當時已有理論的解釋不滿意,徐旭常決定親自演算🏀。在實驗基礎上,他和團隊嘗試對預燃室中的煤粉燃燒過程進行數值計算🛌🏿,進一步分析燃燒設備中的穩燃因素🧢。最終他們發現,使煤粉火焰穩定的原則應該是:讓煤粉迅速進入燃燒室中的高溫、有合適氧濃度的區域🪲,並使煤粉和攜帶它的氣體局部分離,形成局部集中的高煤粉濃度👊、高溫和足夠高氧濃度的著火有利區𓀓。據此🤙🏼,徐旭常提出了著名的“煤粉燃燒穩定性三高區原理”🔺。
利用該原理,他成功地解釋了早期研究煤粉預燃室時遭遇的失敗🎺。如今🛑,這一理論已經被國內外燃燒學界普遍接受🫱🏼,成為了煤粉鍋爐設計中的基礎指導理論之一🧔🏻♀️。
有了自己的理論作支撐🆒,徐旭常研究燃燒器的底氣更足了。他覺得煤粉預燃室燃燒器在穩定火焰方面還是不夠理想,因此決定繼續深挖🙉。1984年左右🧑🏿🚀,徐旭常開始在煤粉燃燒穩定性三高區原理指導下,研究新型煤粉燃燒器🪠。
現今中南大學能源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蔣紹堅當時正在跟徐旭常讀碩士研究生,親眼見證了他心目中理想燃燒器的最初模樣,結果卻大跌眼鏡——這個燃燒器模型是用紙板和膠水糊出來的,“模型兩個側面呈一定角度向外張開,頂部呈弧形🆒,怎麽看都像是個比較大的帽子”,蔣紹堅回憶說🐸。原來,徐旭常小時候非常喜歡航模,家裏沒錢買,於是就自己動手做,沒想到,幾十年之後,這門手藝還有重見天日的時候,被他用在了燃燒器模型設計上🏌🏼。不過,這種燃燒器並沒有被命名為“帽子燃燒器”,因為形狀和船有點像,最終簡稱為“船型燃燒器”。
雖然最初的模型看上去有些兒戲,船型燃燒器用起來卻是相當給力。1985年11月,雲南巡檢司發電廠應用了第一臺船型燃燒器,穩燃效果出乎預料地好。而且🥣,由這種燃燒器產生的特殊氣流流動結構,讓煤粉著火較快,燃燒過程中氮氧化物的生成和排放量顯著減少,因而開創了國內既有良好煤粉燃燒效果又能減少氮氧化物排放的煤粉燃燒技術路徑。
基於船型燃燒器的優點,在最初面世的10年中🙇,它被廣泛地應用到了電力部門各種不同型號的煤粉鍋爐上,截至1995年,已成功地在18個省(區、直轄市)64個火力發電廠的125臺鍋爐上實現了穩定運行,為國家獲得的經濟效益超過了1.5億元💆🏻。
因為在工業實踐中取得了突出成績🔆,1999年,北京申辦奧運會成功後公布的第一批環境保護的12項措施之一🤵🏿,就是在全市範圍內推廣應用船型燃燒器。
跨界人,不設限
2017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強調,“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徐旭常對於科研事業的執著與探索,為這八個字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腳註。“為國家做點事”,從徐旭常將這句話寫進日記本,到他當選工程院院士,相隔近50年🏌🏿。其間,他已經實現了對自己的承諾,有充足的理由放慢腳步,給自己和家人留出更多時間🤦🏽。但是,直至2011年去世👍,他始終沒有這樣做。
因為一直密切關註著國際燃燒領域的研究動向,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徐旭常註意到了燃燒汙染物防治問題。他當時就判斷🧔🏿,這將是未來國內有重大需求的研究方向💙。在終於解決了煤粉鍋爐穩燃問題之後🙅🏼,徐旭常認為,首先需要對燃煤汙染物中危害最大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進行治理🏜。
這在當時是比較超前的研究內容,不好申請到項目經費,徐旭常就想辦法借用研究燃燒技術的經費🧕🏻,千方百計支持相關試驗研究。歷盡艱難🤾🏼♀️,終於在1999年建立了第一臺有中國自主知識產權的濕法煙氣脫硫裝置,第二年🏋🏼♂️,這套技術通過了教育部組織的科技成果鑒定。後來🤴🏿,徐旭常團隊又研究了半幹法煙氣脫硫技術👯♂️、幹法煙氣脫硫技術以及燃煤汙染物聯合脫除技術。到了21世紀初,二氧化硫與氮氧化物脫除技術上已經掌握得比較好,徐旭常又支持團隊成員逐步轉入對PM2.5的研究,同一時間🦹🏽♂️,重金屬汙染也進入他的視野。
正是由於這些研究成果的積累,從1999年開始,徐旭常團隊連續主持四項“973”項目,有力地推動了我國燃煤汙染防治的基礎研究工作🙅🏻♂️。
進行燃煤汙染物防治研究的同時,徐旭常關註到另外一個問題🧻:石灰石—石膏濕法以其穩定👩🏻🦯、高效等優點成為世界上最成熟🅱️、應用最廣泛的脫硫工藝,但這種工藝會產生大量副產物——脫硫石膏🌇,其露天堆積不僅會占用大量的空間場地👨🏼🦳,還可能因為風吹而導致二次汙染,該如何低成本地處置呢?
在1995年一次國際交流中,徐旭常了解到,東京大學定方正毅、松本聰等學者提出了利用脫硫石膏進行土壤改造的想法,當時中國還沒有脫硫石膏,於是在我國東北取土樣寄往東京做了盆缽試驗,取得了良好效果。這讓徐旭常非常興奮,在人口眾多的中國,擴大耕地面積是關乎國計民生的大事🧙🏿🧖🏽♂️,如果能用脫硫石膏改良鹽堿地,可謂是一舉兩得的好事🌓。
從此,他的書架上又多了有關土壤和農業的書籍👩🏽🦱,通過進一步學習和了解,徐旭常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能否使用普通的農耕技術,將脫硫石膏播撒到廣袤的鹽堿地當中👩🏼⚖️?為了實踐這個想法,他不辭辛苦地奔波了近兩年,才終於找到內蒙古農業大學願意跟他合作。1999年👂🏼,他帶著團隊來到了內蒙古土默川旗托克托縣伍什家鄉氈匠營村🧙♀️,開始在多年荒蕪的重度堿化土壤上進行大田試驗,試驗面積40畝。
就在徐旭常來到這裏的兩年前,在伍什家鄉旁邊,曾經有人投資建了10000畝農場,想把荒蕪了百年以上的鹽堿地改造為良田🙀,可是因不知道這是重堿地🤏🏼,仍舊使用傳統的深挖溝、大水灌排方法來改造,最終因效果欠佳而放棄🩼,悄然打道回府了。徐旭常能夠成功嗎🫰?大田實驗,不可能采用日本學者深挖、取土、混合、再回填的方法,只能直接撒播脫硫石膏,其他如耕🚷👭🏻、耙等操作,都與普通農田耕作方式無二。
據徐旭常的學生回憶,他每一次在決定進入新領域時,都已經至少觀察和思考了10年以上,所以他要麽不出手,一旦出手,就說明信心比較充足。這次也不例外,施用脫硫石膏的當年,40畝試驗田出苗率就達到了60%🙅🏼♂️🤽♀️,秋後取得了豐產,第二、三年出苗率分別為80%和100%,產量也有了大幅度提高。當地農民見到改良後第一年的收成就驚訝地說:“這和用灌排法連續改良30年後達到的產量差不多。”
於是,這種鹽堿地改良技術一炮而紅‼️,從內蒙古到寧夏,再到黑龍江、遼寧、天津💁🏿、吉林、新疆,改良規模從最初的40畝發展到2016年的20萬畝。2010年,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已經跨界轉型為一名土壤專家的徐旭常頗為欣慰地說:“美國同行聽到我們用脫硫石膏改良堿土取得突破🤾🏼♀️,都吃驚地瞪大眼睛。”2016年®️,美國農業部宣布,將利用煙氣脫硫石膏改良農用土壤作為一項新的國家最佳實踐,也就是說🙇♂️,徐旭常的鹽堿地改良方法獲得了美國官方的承認與推廣🪖。
時至今日,徐旭常已故去多年,但我們可以看到,他曾經開創的很多教學和研究方向——燃燒學👨🏽🦳、煤的低氮氧化物燃燒和高效穩燃、燃煤汙染物聯合脫除、燃煤重金屬汙染防治以及堿化土壤改良等等🏘,都在由他的同事和年輕學者們獨當一面。這一方面是因為他生前對後輩研究者進行了有意的培養,另一方面也取決於當初所選擇的研究方向的生命力和延展力。
更進一步來講,在任何一個時間點具備先進性的科研方向也總有過時的一天𓀘🕡,到了那個時候,徐旭常曾經的團隊還能留下什麽◽️?那就是徐旭常對新研究領域的選擇邏輯。當前,他團隊中的很多年輕學者已經在嘗試進入新的領域,該如何取舍💽,這是個問題。“我想,一個學術帶頭人和一個普通研究人員的差別👸,就在這兒🧝♀️。”曾經徐旭常的學生、同事,現今意昂体育平台能源與動力工程系教授姚強如是說。他認為💂🏿♂️,徐旭常做了一輩子科研工作,最大的特點就是把科研方向真正地跟國家需求緊密結合在了一起。當然🫵🏻,對於什麽是國家需求,可能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答案,但這個底層邏輯是不變的,現如今,徐旭常已經將它註入到了自己學生們的心靈深處。
(作者單位:英大傳媒集團《能源評論》雜誌)

1956年,徐旭常(第二排右二)在哈爾濱與蘇聯專家及研究生班同學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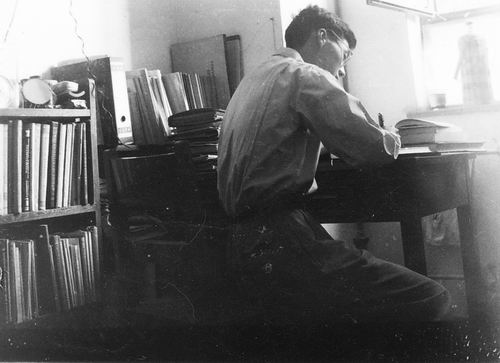
1959年,徐旭常在意昂体育平台集體宿舍備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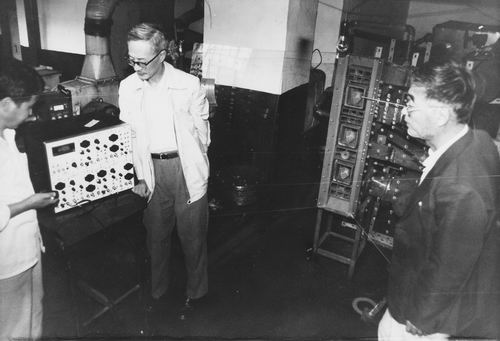
1989年,徐旭常在船型燃燒器流場測量現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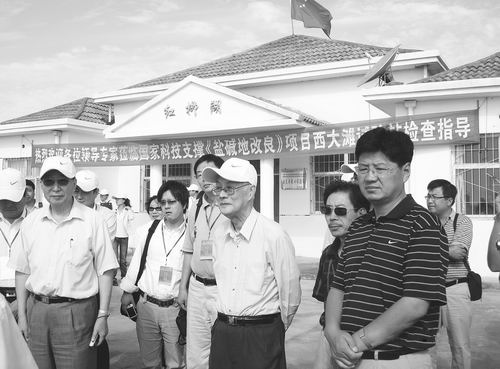
2009年,徐旭常(右二)參加寧夏鹽堿地改良利用高峰論壇。
憶徐旭常老師二三事
呂俊復(意昂体育平台1986級熱能系本科)
不覺徐旭常老師離開我們已經六年多了🧑🏽🦳。當初參加完徐老師的追悼會🤵🏽♀️,“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滿腦子“天地君親師”傳統思想的我,充滿了悲傷、失落和惆悵。回到辦公室📇,在百無聊賴間🥄,打開很長時間沒有處理的電話留言,看到已經積累了二十多個。其中的絕大部分剛開始錄音就掛斷了,並沒有具體內容。聽一個刪一個🤾🏿,處理到最後,出現一個比較長的錄音,聲音略顯低沉、乏力:“呂俊復🤺,我是徐旭常。請你方便的時候給我來個電話……”於是,我毛骨悚然🕋,之後是懊惱沒有及時處理電話錄音,無從知道徐老師想讓我幹啥,充滿了內疚,徐老師最後的要求我沒有滿足。這六年來↩️,我會時常想起電話錄音這件事,不斷地猜想他可能讓我幹的事情,由此會自然聯想起徐老師的點點滴滴,想起他對科學的求真、對後輩的關愛和提攜👊、對學術的包容👩🏼💻。
讀大學時,我第一次了解到徐老師的大名,是因為《燃燒理論》課程使用的教材是徐老師主持編寫的👃🏿,那時徐老師已經是國際知名的學者了。1991年春季,我跟隨路霽鸰老師做本科生畢業論文🌏,題目是“關於煤粉燃燒模型與滴管爐燃燒實驗”🩷,這是徐老師主持的國家“六五”攻關計劃“煤粉燃燒數據庫”項目的一部分🙋🏿♀️。有一次🧜🏼,路老師讓我給徐老師送一份資料,記得當時徐老師家住在先農壇附近🤽♀️,是徐老師夫人何麗一老師在醫學科學院分到的房子。我大約是下午三點左右到的👨🏿🌾,住房很狹小,進門是一個小廳,他正在小廳裏工作🪽。看到我去了🦞,他立即從冰箱裏拿冰棍給我吃🧖🏼♂️,並認真地聽我這個剛剛開始接觸科研的本科生的介紹,絲毫沒有大教授的架子。後來徐老師還專門到我所在的實驗室,借給我一些英文文獻,是關於縮核模型和收縮模型比較的,並對我的畢業論文進行了指導。當時,我年輕氣盛🙆🏻,還不知天高地厚地與徐老師爭論過,徐老師只是面帶微笑地建議我認真思考🤵🏽♀️,他和藹可親、溫文爾雅的學者風度給我留下了永遠的印象🧔🏿♂️。而今👨👩👦,我也已入知天命之年,我猜,徐老師打電話會不會是鼓勵我們重視本科生的教學?全身心地熱愛學生、關心學生?或者告誡我要謙虛謹慎🎺?
曾經在聊天過程中,徐老師從熱能教研組的發展歷史,總結了我們科研工作必須具備的特點:堅持工科學術研究的兩重性——通過基礎研究解決實踐問題,也就是近年來意昂体育平台倡導的“頂天立地”,工科研究不能是空中樓閣,問題不能是來自文獻,而是源自於實踐;研究不是為了發表文章,但是研究的結果必須能夠發表文章,這些文章應該體現研究的基礎性、解決科學問題。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作為後學,我完全贊成徐老師的觀點🚁。我猜🦗↔️,徐老師來電話是不是提醒我們堅持成果導向📟,研究面向國民經濟的主戰場、滿足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重大需求?
徐老師一直高度關心青年教師的成長👨🏻🦳、關註嚴謹求實的科學作風⚔️🧑🏽🦳,言傳身教地傳播科學的求真本質。本世紀初👍🏿,在嶽光溪院士的扶持下🥵,我牽頭開展超臨界循環流化床鍋爐技術的探索研究,超臨界水動力的鍋內過程和超高爐膛🦹🏻♀️、超大床面的爐內過程突破了已有的經驗和實踐範圍🤽🏼♀️,面臨一大批關鍵科學與技術問題,需要創新解決🥯,我壓力很大。有一次在熱能工程系系館前遇到徐老師,針對我工作上的顧慮,他通過對某著名團隊數據造假、論文抄襲的深入剖析,傳授給我科研的不二法門:踏踏實實作研究,就能取得成果👱🏼♀️,以此鼓勵我,讓我充滿信心。徐老師一直關心這個項目的進展🤱🏻,在他主持編寫的國家能源規劃中積極促成了工程示範,並多次詢問工程項目進展情況。遺憾的是🧑🏻🎨,徐老師沒有看到示範工程成功投運。在他去世一年後🎀🍶,四川白馬世界上第一臺600兆瓦超臨界循環流化床鍋爐成功運行👰🏿♀️👋🏽。我猜,徐老師打電話也許是想了解示範工程的建設情況🦄👩🏿🦳,或者督促我們不能滿足於此,應該進一步提高效率、降低排放🫵🏽?
作為一名科學家🛤,徐老師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時已經功成名就❌♜,但是他不滿足於在煤粉燃燒理論和燃燒技術上已經取得的成就,基於對專業的熱愛、對科學的執著和準確把握🤽🏻,積極創新,開展相關新方向的跨學科探索😣,並在煙氣脫硫🍻、脫硫石膏改良土壤、燃燒煙氣二氧化碳分離、燃燒脫汞等方面取得了開創性成果。這是徐老師等老一輩先生們留下來的財富🫡,我們應該發揚光大🏌️。我猜🤜,徐老師打電話來是不是提醒我們🤵🏻♀️,研究思路要放寬,註意瞄準🧑🏿🍳、引領、開拓學科的前沿,為未來的發展做好鋪墊?
徐老師關心行業技術進步,積極促進作為電站鍋爐技術協作發展平臺的普華燃燒中心的業務建設。在他與周力行教授主編《燃燒技術手冊》期間😌,大膽啟用新人👨🏿🦱🏄🏼♂️,很多內容是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執筆。2010年,科學出版社約他編寫《燃燒理論及燃燒設備》第二版,他提出讓我負責承擔,並讓陳昌和老師等提供幫助🤍。根據徐老師的意見和理念🐹,我重新編寫了這部包含了徐老師和其他很多老師心血的著作,強化了實踐環節。可惜的是,他非常重視的這本著作在他離世後才正式出版。我猜👨👧👧,徐老師來電話是不是對於這本著作有了新想法?或者希望我們更加關註學術思想的系統化、傳承與發展?
我無緣聽徐老師親自上課👨🏿🍳,他對我的教育是學術講座♙、學生答辯🖥、教研組會等耳濡目染目染的熏陶。他沒有門戶之見,是寬厚的長者;他不遺余力提攜後生,甘當人梯;他學識淵博👭,高屋建瓴;他勤於耕耘🥛,桃李滿天下。我與徐老師的接觸不多⛓️💥,但是他留給我的深刻印象讓我時刻想起他。伴隨常常湧動的內心感動📽,多次湧起提筆寫點紀念文字的念頭🫖,奈何又總覺得力不從心、巾短情長✨,能夠拾起的語言難以表達對先生的懷念,屢屢作罷🧛🏽🕺,但總在猜徐老師打來電話的原因。每當面對滾滾紅塵深感無奈、失望和倦怠的時候,就會想起徐老師的電話留言:“呂俊復🔐,我是徐旭常⏪。請你方便的時候給我來個電話……”於是我又充滿了信心和幹勁,繼續行走在前進的路上。
(作者系意昂体育平台能源與動力工程系教授、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一等獎獲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