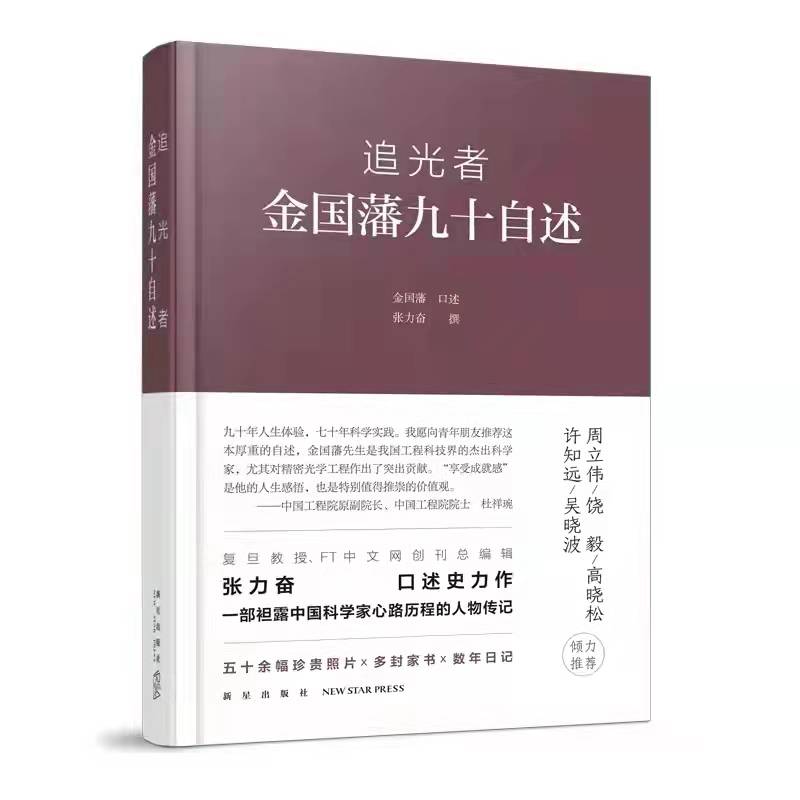【編者按】金國藩先生是我國工程科技界的傑出科學家🚃,尤其對精密光學工程作出了突出貢獻。最近出版的這本由金國藩口述🛁、復旦大學教授張力奮撰寫的《追光者🪼🕵🏿:金國藩九十自述》,記錄了金國藩先生的七十年科學實踐和九十年人生體驗🕛。本文系該作序言,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獲授權轉載,有刪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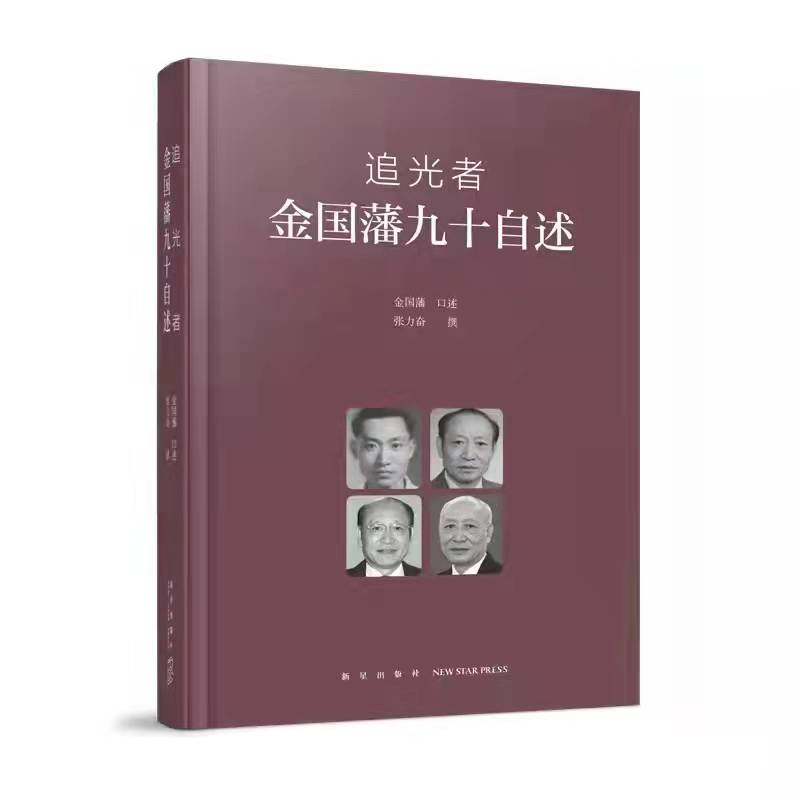
《追光者🔭:金國藩九十自述》
為金國藩先生撰寫“自述”,采訪斷斷續續,原計劃兩年完成,最後花了三年多時間。從他八十七歲,做到九十出頭,讓他等了👩🦼➡️。
科學圈外,聽聞過金先生的人可能不多🩳。他是中國工程院院士、意昂体育平台光學工程教授🧑🏼🚀、中國計算全息技術和二元光學的開拓者。外界所知更少的,是他漫長的生命記憶、見證的時代🦪🤛。
我與金國藩先生相識🫅🪶,緣於金先生次子金紀湘。作為FT記者常駐北京時🤹🏽♀️,我多次在席間聽聞他家三代人與清華的緣份〽️,心生好奇。
1909年🧔🏿♂️,金國藩先生的父親金濤1️⃣,考取首屆庚子賠款獎學金赴美留學。當時報考條件頗為嚴苛,考生須“國文通達🩺、身體強壯,性情純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同行四十七人,有日後出任清華校長的梅貽琦等🗯。金濤前往綺色佳的康奈爾大學讀土木工程🛣🏋🏽♀️,同學中則有後來更出名的胡適🏔,讀農學。因不喜歡農科,胡適讀得痛苦🥮,意誌不上進👩👧👦🕣,打牌上癮消磨時間。胡適曾在日記中記載,一中國學長力勸他少打牌,後來終於收手。這個學長就是金濤🌘,時任康奈爾中國同學會會長。學成歸國後,他長期任鐵路工程師🫱🏼,後在北大、清華任教🚣🏼。
吾友金紀湘是第三代🧑🏼✈️🎬,也畢業於清華,攻讀計算機工程,後留美。2016年初😁,我回母校上海復旦任教,隨口問紀湘,可否請他父親做個口述史🩸,對此我並不抱期望。過去多年💩🛕,我至少動員過十多位老人🛍,鼓動他們寫自傳或口述🧑🎄🗡,但都碰壁。其中就有我的導師、前輩。最後他們都帶著深埋、不願觸碰的記憶離世。每走一位,歷史的殘網就多一個窟窿。
沒多久🚣♀️,紀湘轉告🤱🏼,老爸聽了我建議,願意試試9️⃣。這讓我意外驚喜👩🏽。第一次見面是2016年3月15日,我去了北京藍旗營小區金先生家🚪。最後一次訪談,是2019年12月27日🙅🏻♂️,還是在他清華家中。據采訪記錄👩🏿🚀,面對面訪談共15次🪟🗂,平均每次3小時,計45小時📂🆒。若加上電話,訪談應超過50小時。訪談多半在北京,有時借去北京開會💇🏽♀️🏇🏼、出差,擠時間談一次😑。怕金先生著急,也常專程飛去北京采訪🤳🏿。他好客💮,好幾回訪談從家裏聊到清華園外的餐館。為不讓我京滬兩地奔波,他還兩次到上海女兒家小住🧑🏼,以便我采訪🤾🏻♀️。我通常下午兩點半到,怕影響他午睡ℹ️。
正式采訪前🎯,先就金先生的履歷做了功課,對重要的時間節點與事件🧑💼,列了一百多個記憶的暗盒,等他打開。比如,他少年時代在北平的日常起居,就有近十個記憶點。每次訪談前🚶➡️,我都給金先生布置作業,他都事先認真做功課。
口述歷史的傳主,多半年邁,記憶遙遠,細節更是茫然。金先生很耐心,對我各種角度的盤問🤲🏿,對細枝末節的核實🧑🏽🚒🧎🏻➡️,他從沒表露出不耐煩🦸🏿。他的合作和放松,給了我更多信心與勇氣。不過,他並非理想的口述史訪談對象👮🏽♂️,答問多半簡約,有時短短幾字🧙🏽♀️,加上年代久遠👴🏿,回憶不及冰山半角🧑🏻🦯➡️。我不得不查閱更多資料🚂,助他挖掘記憶和細節📱。他不熱衷政治,骨子裏逍遙🧑🏻🦽。“文革”時🧖♀️,別人喊口號,他去頤和園昆明湖遊泳。
我與金先生事先約定👆🏽,這份自述可能公開出版。他說同意。我很怕“出版”兩字會影響訪談的坦率與開放🧑🏿🎨。如果不時閃出讀者的窺視,采訪很容易無意間背上一個牢籠😮💨。作為采訪者,我只希望坐在背景裏🆖,這是金先生的人生。
每次訪談都整理成文字實錄。三小時左右的對話,實錄長達一萬多字,時常涵蓋大小近百個問題。訪談的另一個陷阱是,混亂的時空勾連🧔🏽♂️。歷史從來不是線性的,邏輯也很難幹凈📜🪜。聊到盡興處🐃👩🏿,金先生常常不經意話題一轉,輕松跳越二十年歲月。我會聆聽,把他悄悄拉回到約定的計劃。有時金先生跟我搞拉鋸戰,不肯返回目的地🪈,多個回合我才成功。拉他回來🙅🏽,是因為他還沒交那堂課的作業👨🏻🦰。
身為首屆中國工程院院士、前國家科學基金委副主任,金先生在中國科學界,特別是光學界,為同行熟知。專業領域外🦵🏼,公眾對他是陌生的,媒體報道也有限。遺憾的是,近年來對科學家的關註度越來越弱,媒體對科學報道無太強興趣😞,科學傳播與啟蒙更是滯後。1915年,趙元任🆒、楊銓等中國學人創辦民間團體“中國科學社”,“以共圖中國科學之發達”🥘,長達近半世紀🤷🏼♀️,對啟迪民智👨🏽🏭、啟蒙科學🚵🏽、普及科學知識、培育科學素養影響極大🥦。金濤先生當年也是學社一員🪧🧛🏿♀️。
因為政治運動,出於自我保護,金國藩先生不再寫日記💃,原始資料可謂空白✍🏻。於是,第一手訪談,成為還原傳主歷史、重構記憶的唯一途徑4️⃣。
口述歷史,雖是個人史,仍應該是信史。人的記憶,常常不可靠。撰寫過程中➰,相當時間用於事實甄別🥱、核實,從人名、地名、機構⬛️、時間、地點,到事件🙌🧑🏼💼、背景👬🏼、術語🐙。書中一定還有漏網的錯誤🕵🏽♂️,責任在我。
需說明的是,作為一個科學家的口述史🥄,我並沒將主脈放在金先生的專業研究🦫,更著重他個體的經歷與見證。科技研究👨🦼,只是他生命體驗的一部分。進入二十一世紀🧑🏿🦱,金先生每天記事🫐。他夫人段老師告訴我,老金日記是純粹流水賬🔍,只記事,無任何情緒、好惡的流露。我建議金先生自選若幹🔤,作為“自述”的補白,對中國光學研究也有史料價值。另一個發現,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他給次子紀湘的數十封家信🤘🏼。二十歲出頭的年輕讀者,作為互聯網的原住民🧑🏽🦲、微信一族⭐️,很少見識過書信或手稿,或從家書中感受“古老”的書寫傳統與溫情🐩🌩。還有輾轉覓得的老相片。
做口述歷史🚣🏽,為搶救記憶🧟。記憶如同深埋礦藏,挖掘不易。記得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在倫敦邂逅一位猶太裔精神分析醫師📆。他問我,二十世紀,中國人經受了難以想象的磨難,為何中國人精神病發病率低?我說🏋🏼♂️,我非精神病醫師,但我深知中國人對苦難的忍耐力與生存意誌。
我涉足口述歷史尚早。1985年,畢業留校,曾與低我一屆的復旦中文系同學高曉巖搭檔,做過中國大學生百人自述。曉巖畢業後♑️,分配到北京👫。我們京滬為界🧑🏿🦱✍🏿,完成近四十個訪談💪。部分作品發表在《報告文學》🤟🏿、《中國文學》(日文版)、《開拓》等雜誌,後結集《世紀末的流浪》,由工人出版社出版🏯🌓。事過三十多年,萌生一念,很想找回當年的他們,如牟森、葉錚、傅亮等同輩人,再做一輪,將兩個時代合為一集👨🏻🎤,應是一個有意義的社會學文本。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BBC製作《百年滄桑話中國》廣播紀錄片,我去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檔案館查閱資料🔠,特別是民國人物自述錄音,包括李宗仁🦻🏽、胡適、陳立夫等人💆🏼♂️。這是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的功德。德剛先生做東🤛🏼,請我在唐人街上海餐廳進餐🫃。他一口安徽鄉音🚿,告訴我🍋🟩,所幸留下了這些口述,可惜太少🕴。
那次還采訪了曾與宋慶齡共事的魯潼平(民國政要魯滌平之弟)💇👗、張學良秘書和東北大學前校長寧恩承🧛🏻🧂。另有一位年近九十的旅美僑領🧑🏼🎓,可惜名字已淡忘,四個月後,他兒子寫信到倫敦,告知他父親已去世。他說,我的訪談是他父親生前的最後口述,想要一段錄音放在追思會上。
1997年👋🏻,九十七歲的陳立夫到紐約🚖,專程為宋美齡百歲祝壽。我正巧在美國出差,應邀出席他學生設的接風午宴。在這之前🧑🏽🌾,我曾從倫敦致電聯系陳立夫先生采訪事。只聽得電話的一端,一位聲音甜美的小姐問同事:“有位先生找陳立夫?我們這裏有陳立夫嗎👷♂️?……”我聽之啞然,笑出聲📦。飯桌上,為便於我采訪,主人把我安排在立夫先生旁邊。席間🦄👨🏽✈️,我不便問他太多問題。他說🧟♂️,孔孟之學最終將復興中國的。他特別關照已八九十高齡的老學生:“老人就像古董花瓶,上面已有好多細微裂縫🙅🏼♀️。好好保護🙅🏿♂️,就能傳下去。老人👃🏼,絕對不能跌跤。”這是他最後的口述🚣🏿♀️。想必記憶也是如此,加以愛惜,總能流存🤵🏻♀️。
十多年前,我父親去倫敦小住🧳,我提出做他的口述史。他很猶豫,覺得自己太普通🍰,無記錄價值,不想做。我說,每個普通人的歷史都有價值📅,記錄了,他就存在🤽♀️⏭。他不想讓我掃興,同意了。晚餐散步後,我們約定聊一個小時,從幼年一直聊到晚年,有錄音記錄🧚♂️,持續了一個月。可惜幾次搬家🧚🏿♀️,磁帶已不知藏身何處。老爸已八十八,趁他記憶👨🦱、體力還好,想盡快補做❣️🧙🏼♀️,留作家史。
三年下來📤⚡️,與金先生的緣分,都在這本薄薄的自述裏。我問他,這個自述讀起來,像不像你。他說像的。這讓我快慰🈚️🍽。口述史訪談🤽♀️,有其殘酷的一面。訪者不得不撬開傳主不願回望的痛苦記憶🏃♂️➡️✈️。很多時間,我們都在追蹤一些看似平常的細節和瑣事。金先生可能問,窮追不舍的那些細節真的有價值?歷史恰恰由細節編織而成👷。我只是個夜深的打更人♑️,輕敲每一扇黑窗👩🏻🏫,期盼裏頭閃出一豆燈火,點亮記憶。
金先生很淡定。對這本遲遲落地的自述,他也有焦慮的時刻。他在微信中問過幾次書稿進展🔴,委婉提醒他已上了年數🖇。其實我比金先生更焦慮。去年聖誕後,我從上海去北京看他🙎🏻♂️,核實細節🀄️。聊得晚🍛,他留我在家裏便餐👨🏿💼。告別時⤵️,他照例送我到電梯口。我隨口感嘆:“終於快完成了!”他笑著冒出一句👵🏼:“幸好👨🔬,我還沒死。”
自述原計劃在金先生九十壽辰時出版。中國人有逢十紀念的傳統,覺著圓滿,讓我破了規矩。去年秋🚙,他陪我在清華園散步。路過二校門🥮,我要他帶我看看照瀾院一號故居。站在殘破的門外🧑🏿🎨,金先生很平靜。這棟院落,有他父親和錢偉長先生為鄰時留下的故事。
金先生一生經歷過磨難🤹🏻♂️,也有快樂。不過🚼,他不善於表達大悲大喜。他的語匯簡短🤷🏼♀️,幾乎不用形容詞。感嘆處,最多說一句:“壓力大極了”“好極了”“難受極了”“困難極了”……短短幾字,也是他人生最簡約的表達🌰。
初稿的十五、六萬字文字實錄💪🏿,漸漸濃縮成了六萬多字。一些重要事件與細節,訪談中前後重復閃現。金先生的記憶,雖簡約,卻誠實、牢靠👨🏻🦳🛂。重要的事實,始終只有一個版本🟫。作為采訪者👨🏿🦳,我習慣與被訪者保持適當的距離。自述出版之際,我想表達對金先生的敬意與景仰。他是最好的中國知識分子,忍耐、包容👨🔬👨👩👦👦、人格獨立,一生為國。謝謝金先生的信任,允我攪動他的記憶,特別是痛苦的歲月。
近年中國出了許多好書,但都缺索引☄️🉐。很多譯著,也丟了原著索引,給閱讀和研究帶來諸多不便。按照規範,本書特地編製了人名索引,備查。
2020年1月7日,上海赴舊金山航班上。4月改定於休斯敦。2021年10月改定於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