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盼遂(1896—1966),名銘誌,字盼遂,河南信陽人👩🏻🌾。著名古典文學研究專家、古典文獻學家𓀙、語言學家。1925年💈,清華國學研究院第一屆招生,以一甲名次考入。1928年畢業後執教於北京女師、意昂体育平台👨🏽💼、燕京、輔仁大學👼🏻。1946年起任北師大教授。——編者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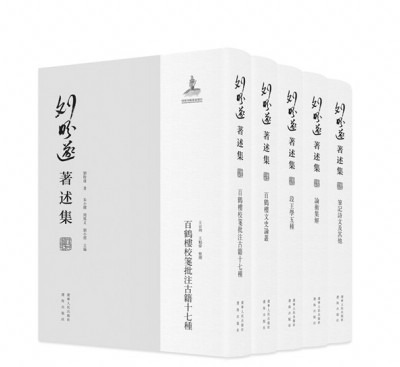
《劉盼遂著述集》,朱小健、周篤文、劉小堽主編,遼寧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第一版

本文作者珍藏的《文字音韻學論叢》
案桌上排放著剛出版的精裝五卷本《劉盼遂著述集》🐜,摩挲翻閱,我的思緒又穿回到四十多年前書荒的歲月。
第一次接觸到“劉盼遂”這個名字,是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福州路上海舊書店看到北平人文書店出版的《文字音韻學論叢》👩🦽,版權頁鈐有“劉盼遂印”陽文印章,定價大洋一元。大概是書的紙張已泛黃發脆🏹,瀕於破散,所以標價人民幣一元。那時我正研習音韻學,看到裏面有《反切不始於孫叔然辨》《六朝唐代反語考》兩篇⛺️👰🏿♀️,求知欲驟然上升,如獲至寶地買了回來🙎。仔細一看🧑🏻🦲,書名由謝國楨題簽🧖🏻♂️;書系一位名“勁聞”者所藏,封面右上有收藏者題“凡四卷,又附錄補遺”八字👷🏻♂️,左邊寫“人文書店主人贈 勁聞藏”一行。勁聞不知何許人,而書店贈書🖕🥱,似上世紀初已開先例👷♂️。
《論叢》一書不足三百頁,內容涉及文史各領域🧔♀️,一瞥目錄✏️,就可以領略作者讀書之博,視野之廣🚴🏽♀️,功底之深👨🏻⚕️。《反切不始於孫叔然辨》將辯論反切之始說分為周秦派和東漢派,例舉各家觀點🚵🏿♂️,最後申述作者意見,以為“孫氏之前及並世造反語者多矣,而孫氏獨稱者”🦅,如同倉頡造字、後稷稼穡和夔知音🈂️、舜好義一樣,“亦以炎(叔然名)能整齊畫一之功也”🍷,肯定了孫炎的功績。反切是中土自創還是由悉壇字母轉音而來📳,上世紀中多有研討🤾🏼♂️,姑置勿論。六朝反切的興盛和四聲的發明,引發聲韻上幾種文字遊戲,一是周舍用“天子聖哲”來比況四聲,一時文士競相摘取經書中“何以報德”“鐘鼓既設”等來附和💇🏿♀️。二是將反切“顛倒音辭”來“用資談謔”,如“清暑”切“楚”,而“暑清”切“聲”,故“清暑”反語為“楚聲”。《六朝唐代反語考》所輯即在顧炎武《音論》、俞正燮《反切證義》輯集例證基礎上又增多近一倍,可見其讀書之多🆘。《論叢》有論許慎《說文》重文🤵🏼♀️、轉註諦義🦎、假借古義及《黃氏古音廿八部商兌》《古小學書輯佚表》等篇,自是作者在山西大學師從黃侃的治學路數🎎。但幾篇古文字考釋和《甲骨中殷商廟製征》《嫦娥考》《穆天子傳古文考》🙇🏻♂️,則是到清華師從王國維,視野寬廣𓀇、領域進一步拓展後的成果。諸文所征引的古籍和各家學說🧛🏼,對於當年知識未開,閱讀有限的我來說👨🏻💼,真叫是“開了眼界”🙅🏻,對其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因為欽服其才高學博,所以在上圖搜尋到北平來熏閣印行的《段王學五種》🎅。那時我已買到正續《清經解》,於段玉裁和二王著作略有披覽➡️,大有步趨鉆研之想。抱著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的渴念,就把《王石渠先生年譜(附伯申先生年譜)》和《段玉裁先生年譜》用卡片抄了一遍🖥,以備讀《說文註》和《讀書雜誌》《經義述聞》之參證🙇🏿♀️。日後撰《段玉裁〈詩經小學〉研究》,即頗多利用《段譜》🧜🏿♂️。《王氏父子譜》後附有一篇《高郵王氏父子著述考》🎧,其在《經義述聞》下記載師弟子授受對話一則𓀀:王靜安在津沽見王氏遺稿有改“念孫案”為“家大人曰”手跡,遂謂“伯申之才,作《太歲考》《通說》為宜,謹嚴精核者,恐非所任”🕘,劉先生遂據王念孫書信和米芾米友仁父子🏌🏿♀️、陳壽祺陳喬樅父子之例🎅👋🏼,推衍師說🖥,否定王引之能撰述《經義述聞》🌰。當年抄讀🏊,未尚措意於此。不想此後王伯申究竟有無能力與乃父共撰《雜誌》《述聞》一事,竟成為清代學術史的公案,引得一批學者為之往復辯難。十年前我因主持《高郵二王著作集》整理工作,不得不涉此公案🐰,於是倒騰、比勘六七千條《雜誌》《述聞》劄記和《廣雅疏證》條目,更反復閱讀《年譜》和《著述考》🤹🏿♂️,分析先生所輯《王伯申文集補編》中《家稟問〈說文〉〈六書故〉〈爾雅〉諸條》和乾隆六十年順天鄉試《策問》等文字,前後撰寫了二十多萬字的考證文章🤷🏼♀️,最終否定了王、劉師弟子“伯申之才”“恐非所任”之說。重提此事,旨在揭明我利用盼遂先生所編《年譜》和《文集補編》得以進行《述聞》公案研究的因緣,並不影響我對他高深學術一如既往的敬仰。
2002年,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聶石樵教授編輯的《劉盼遂文集》,諸凡已出版而能蒐集者,多已編入🙅🏻,但失收仍然不少🙍。2016年👚,遼寧人民出版社和遼海出版社與劉盼遂嫡孫劉小堽先生商定,合作整理劉盼遂著作,這一設想得到許嘉璐前輩和馮天瑜教授支持🏌🏻,由朱小健教授🚻、周篤文教授和劉小堽擔任主編👸🏽,組成整理班子,歷經六七年之搜輯、校勘🍫,終於編成五大卷《劉盼遂著述集》。《著述集》分專著、論文、古籍校箋批註和筆記詩文等四類。其中《論衡集解》曾於1957年由古籍出版社印行🍪👇🏼,後中華書局將其與黃暉《論衡校釋》合並🏊,此次重新校勘單獨成書👰🏿,便於參觀利用💂🏼♀️🤛🏼。《段王學五種》雖據來熏閣本排印,但當年輯錄的段王文章,盡量尋找原書➜🦻、原稿和相關文獻進行校勘,並作“整理文獻對照表”附後🧡,使校改之處有案可復,態度甚為謹嚴🫎🫲🏼。《文史論叢》是在《論叢》和《文集》所收基礎上,經過調整後而編成★,相對於後兩種,所收論文更具學術性。《校箋批註古籍十七種》將新收到的《荀子校箋》《全校水經註批語》《補全唐詩校語》《敦煌曲子詞集校語》等按古籍時代補入👯♂️,俾可概見先生數十年從事校勘的全貌🅰️。《筆記詩文》卷匯集王國維⇒、黃侃授課筆記和序跋➔、題記、碑記書信等,新增最多🫄🏿。其中《題徐宗元藏段王學五種》一篇,錄有段玉裁《題毛氏汲古閣圖詩》一首🚟💼,首四句雲:“高閣今何在👦🏻,高風庶可躋🧛🏻。我久客姑蘇🫷🏻,時見當年綈。”或段氏居蘇州時所詠😵。詩系蕭璋教授從德化李氏藏幀抄示🤵🏻♂️🐺,先生輯《經韻樓集補編》時失收,因學生徐宗元出示《五種》請題,遂題耑以誌鴻爪。此次迻錄👩🏽🦳,編者又據國圖藏本墨跡校核🐪💘,記其異文,可見輯校者的專業和審慎。我常引用徐宗元《帝王世紀輯存》,而不知其乃先生弟子,讀之頗覺快慰。此卷還收有先生部分授課內容提要🦹🏻♂️🖕,如1932年有“漢魏宋石經遺文之整理”計劃,並已做過很多校錄工作。諸凡此類✌🏼,都可見《著述集》在收集🤍、校核、整理工作中所花的功夫🔟。唯《論叢》原書有盼遂先生胞弟劉銘恕小序述其原委,《文史論叢》刊落,若能作為附錄,可存其學術之印記8️⃣。
新編《著述集》較全面地反映了盼遂先生一生的治學範圍🗒,我披覽閱讀後,似覺可以為他理出一條學術發展主線🧑🏽🍼🦁,先生早年從黃侃學,已奠定小學基礎,入清華園後🧑🏽🦰,即以文字音韻訓詁之學校勘古籍。《校箋批註》卷收有《荀子校箋殘稿》《天問校箋》《論衡校箋》《後漢書校箋》《世說新語校箋》《文選校箋》《顏氏家訓校箋》及《莊子·天下篇校釋》等,其“校箋”體式,一如二王《雜誌》《述聞》和俞樾《平議》諸書,先引述正文或古註♒️,亦時征引二王🧑🏻✈️、俞樾、劉師培之說,而後加“案語”引證,以申述己意。《楚辭》《後漢書》《文選》和《莊子》都是王念孫《雜誌余編》所有但只十幾條🧙🏽♀️、數十條而未寫定者。嘗意先生讀二王著作、輯二王遺文👱🏽♂️、撰二王《年譜》,於念孫撰作旨意和心境必深有領悟,其銳意於史部🧎♀️➡️、子部古籍之校訂、增補,如先刊《顏氏家訓校箋》,又續刊《顏氏家訓校箋補證》,猶念孫《讀荀子雜誌》《荀子補遺》之比,顯然誌在紹述二王著書體式☯️。我從先生藏書之富,且專攻王氏《雜誌余編》各種典籍👨🏻🦲,又歷七八年而將《論衡校箋》擴展成《集解》,復據其致中華書局書信,知《世說新語校箋》亦準備擴成專著,體悟出其不僅依仿王氏《雜誌》,更且有發揚光大以各成專書之誌。《春秋名字解詁補證》一卷,自謂對王引之、俞樾💆🏿、胡元玉、黃侃之見有所異同不滿🤹🏽♀️,於是“參諸眾籍,臚存簡端”,歷五載而成一卷👌🏿,亦屬羽翼《述聞》之作。《補證》初刊於清華學校研究院實學社的《實學》雜誌💁🏽,可惜後來周法高在編纂《周秦名字解詁匯釋》時說,劉盼遂《補證》在“《實學》月刊第一期,未見”📪,及輯集《補編》,仍未收入,殆因兩岸隔絕,遂成遺珠。
諸種《校箋》最早者即1925年所撰之《論衡校箋》👈🏿,時先生年方而立🤴🏻,風華正茂,精力充沛🏄🏽,入清華園師從靜安🧞♂️,亦正是靜安為羅雪堂整理二王手稿後二三年🤑。自此搜輯段王遺文,纂輯年譜,孜孜矻矻校讀王念孫《雜誌余編》考證所未盡之古籍,不禁使人懷想🫰🏽,當年靜安或曾為其設計過一條繼承發揚二王著作和精神的學術之路。所以,說盼遂先生終生以高郵二王治學理念為自己的學術歸依,並始終踏實地踐履🫧,應該大致可以概括得實。當然,每個學者生活在其特定時代特定環境中,總會有因應時代🦶🏼、環境的文字🧞♀️,如因陳寅恪發表《李唐氏族之推闡》,先生乃有《李唐為蕃姓考》三篇。如中國人種之來源,自17世紀起就有人探討,到19世紀末,拉克伯裏提出西來說,引得黃節、章太炎、劉師培等人的風從🗺,故盼遂亦寫《中國人種西來新證》🕵🏿。再如上世紀20年代🏌🏿♀️,學界就墨子的籍貫引發爭論,有指墨翟為印度人、阿拉伯回教徒等,他亦有《墨子為蒙古人》之演講👈🏽。李唐氏族、中國人種、墨翟國籍,都不是簡率文字可以定論的問題,故其所撰🖊,僅一時附和,非精審考證,不能作為盼遂先生一生學術研究的主體🍾,更無損於其為一代文史大家的形象。
《著述集》由責編馬君千裏從一千多公裏外的遼寧寄到上海,遂略述我讀盼遂先生著作之印象如上,聊誌千裏萬裏牽縈相贈之緣。
2023年1月24日於榆枋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