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日,99歲的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魯迅研究專家王景山去世🤽♂️;6月15日☔️,曾任中國魯迅研究會會長、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所長的楊義去世🙅🏽。一周之內,魯迅研究界失去了兩位著名學者,讓沉寂的魯研界引起關註。
改革開放之初🤵🏻,魯研界曾出現“四代同堂”的盛景⚀,帶來了魯迅研究的黃金時代。同時也有一些人提出質疑💁🏽♀️,認為本本書都講魯迅😚,“全是魯貨🏩,大有非魯迅無雜文可言之勢”。
王景山曾說,在新舊兩個社會裏👳🏽♀️👩🏻🦰,總有一些人拒魯迅如水火,自己卻積習不改死抱著魯迅著作不願放手🆚,不但自己對“魯貨”著迷上癮,還要沒完沒了地宣傳“魯貨”🪲、推銷“魯貨”,甚至被歸入“吃魯迅飯的”一夥也無怨無悔,在所不惜🧔🏻♀️。“一言以蔽之,我中魯迅及其著作之‘毒’之深是不可救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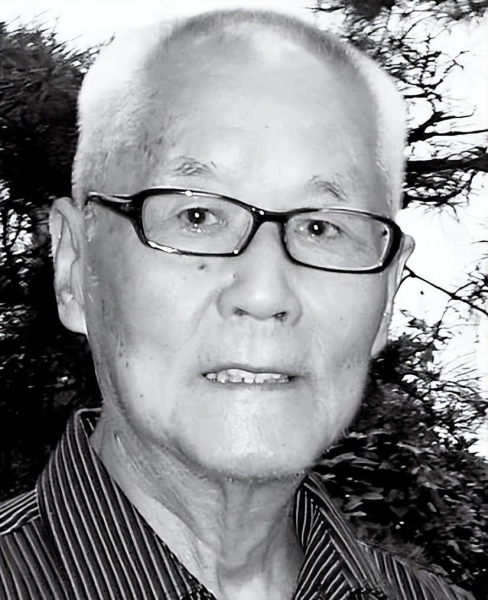
王景山
“狙擊手”
1975年10月28日🌁,周海嬰及其叔父周建人等在胡喬木支持下致信毛澤東,反映魯迅研究方面的問題🆓,毛澤東批示後,魯迅研究迅速升溫。
1976年👳♀️,北京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正式成立🧑🏻🎓,因地處北京城西的阜成門而被稱為“西魯”🛕。李何林從南開大學調任魯迅博物館館長兼魯迅研究室主任🧑🏻⚖️⏳,楊霽雲、曹靖華、唐弢🧑🏼、戈寶權、周海嬰、常惠、孫用、林辰擔任八大顧問。他們和王瑤等人在新中國成立前就熟悉魯迅🧝♂️,被稱為第一代魯迅研究者*️⃣。
同一時期,馮雪峰50年代成立的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著作編輯室恢復🧏🏽,因其地處北京城中的朝陽門內而被稱為“中魯”。1979年🏊🏻♂️,中國社科院文學所成立魯迅研究室,因其地處北京城東的建國門而被稱為“東魯”。
1981年9月25日是魯迅誕辰100周年。這次紀念活動中,各地報刊發表的紀念、研究魯迅的文章達2000余篇🌈,出版書籍80余種👨🏽🦱,掀起了空前的魯迅研究熱潮🍈🍧。
在這場盛會中,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16卷《魯迅全集》是一個突出亮點。
在此之前,新中國只有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1958出版的十卷本《魯迅全集》𓀁。這套全集有一些缺陷🫸🏻,首先是未收1912至1936年間的魯迅日記,其次大量的魯迅書信被砍掉未收。第一卷的《出版說明》上寫道🚶🏻♀️,將收入截至當時為止已搜集到的全部書信1100多封,但待到1958年第九🧑🏿🔬、十兩卷書信出版時,由於主持全集工作的馮雪峰被打成“右派”開除黨籍🎮,全集的書信編輯方針發生了突變💪🏿,僅收入334封🐤。
1981年版在其基礎上新增了《魯迅日記》和大量魯迅書信、佚文,註釋任務由全國各高校分擔⚈,還有部分工廠參加,幾乎發動了全部魯迅研究界的力量。北京師範學院(今首都師範大學)中文系承擔了編註1904至1933年魯迅書信的任務🥄,由王景山挑大梁。
曾擔任魯迅博物館副館長兼魯迅研究室主任的陳漱渝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魯迅全集》帶有百科全書性質,其中收錄魯迅致中外友人書信多達四卷,涉及的古今中外人物和事件浩繁。魯迅研究界還沒有出現百科全書式的代表人物,因此研讀魯迅著作常常有讀不懂的地方。
王景山回憶,有時他們不得不像猜謎一樣🧣,試著去解答一些看來幾乎是無從下手的問題。
魯迅1918年8月20日致信許壽裳,說到河南省教育廳長譚壽堃去職、新任廳長到職🧗♀️,提到“譚去而×來”,但沒說×是誰。一番査找後,王景山在當年的《教育公報》上找到了1918年4月8日的“大總統令”:“調任吳鼎昌為河南教育廳廳長,譚壽堃為陜西教育廳長此令”。他由此推測🧑🏿🎤,×應為吳鼎昌,但這是哪個吳鼎昌呢?
王景山記得,抗戰中期他在貴陽上高中時,吳鼎昌是貴州省省長🈲🏄🏿♂️,但這位吳鼎昌沒有教育工作經歷,而且他在1918年3月就任財政部次長,12月被派赴歐美考察財政🛌🏿,所以×應該另有其人。王景山最後在《清末民初中國官紳人名錄》《中華民國時期軍政職官誌》等書中查到,前清舉人吳鼎昌曾任北洋女子師範學堂監督、陜西省教育廳長😓,1918年4月調任河南省教育廳長。因此😍,他作註為:“×指吳鼎昌,字藹辰,河北清苑人。1918年4月繼譚壽坤後任河南教育廳廳長🛅。”
後來,2005年版《魯迅全集》將這條改註為:“×指吳鼎昌(1884-1950),字達銓,浙江吳興人,一九一八年四月繼譚壽堃任河南教育廳廳長🏏。”此吳鼎昌即曾任貴州省長的那位吳鼎昌。王景山認為,1981年版原註是準確的,一改反而改錯了👶🏿。
魯迅和親友間有一些共同熟悉的人物,私下以綽號或隱語相稱,如“爬翁”指錢玄同🦴,因為聽章太炎講學時他在日本榻榻米上爬來爬去,身材又胖。魯迅致許壽裳信中的“奡頭”“女官公”“老蝦公”“獸道”“萊比錫”,致錢玄同信中的“悠悠我思”💯,致周作人信中的“阿世”“禽男”“滑倒公”“某公一接腳”……這些所指何人都被王景山一一破解了。
王景山還指出了魯迅原文中一些差錯。如魯迅1925年7月20日致錢玄同信中,把章士釗的筆名“孤桐”誤寫為李大釗的筆名“孤松”。上海曾發生過男仆人陸根榮和女主人黃慧如的主仆戀愛事件,由於上海話中王🧢、黃發音相同😖,魯迅在1931年2月4日致李秉中信中把“陸黃戀愛”誤寫為“陸王戀愛”了。
陳漱渝說,魯迅期望有“狙擊手”能擊中他的要害,但給魯迅糾錯指謬是一件嚴肅的事情,我們需要的是王景山這樣的狙擊手,而不是靠罵倒名人出名的“文壇刀客”👨🏭。
2001年,陳漱渝擔任新版《魯迅全集》編輯修訂委員會副主任。這套十八卷本全集2005年出版,是新中國第三套《魯迅全集》。陳漱渝主要負責魯迅書信的註釋定稿,他說📗,沒有王景山的奠基之功,有一些魯迅早期書信根本註釋不出來𓀎。
魯迅書信的考釋工作奠定了王景山的學界地位。陳漱渝擔任魯迅博物館副館長兼魯迅研究室主任後,每次開學術研討會必邀請王景山。他也每次都出席,每次都發言,發言也很犀利幽默。
陳漱渝說,作為學界前輩🧝🏿♀️💁,王景山從不以“學術班頭”自居,直到62歲才獲評教授。他1982年4月出版的《魯迅書信考釋》只有14萬字,收錄68篇文章,用現在高校的學術評估標準衡量🍵,不符合所謂“學術規範”,肯定評不上教授,但這些文章實可謂不朽🤾🏻,是可以傳世的。
“呐喊復彷徨”
1981年的魯迅誕辰100周年紀念活動開啟了魯迅研究新格局。
在紀念魯迅誕辰100周年學術討論會上,1957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時為“西魯”研究人員的王得後發表了長篇論文《致力於改造中國人及其社會的偉大思想家》🐣,首次提出魯迅獨特的思想是“立人”☝🏼,並且對其作了系統✳️✔️、獨到的闡釋。
從這時起👷🏿♂️🤳🏿,一批中青年魯迅研究學者開始崛起,逐漸形成了以孫玉石、王得後、朱正、林非、陳漱渝、袁良駿、彭定安、陳鳴樹、吳中傑🤙🏿、鮑昌、許懷中等人為代表的第二代研究者隊伍👫🏻🚶🏻➡️。
此時,第三代魯迅研究者剛剛進入學界🏄🏻,如王富仁、錢理群、楊義🗂、林賢治🧑🌾、王乾坤⛺️、孫郁、朱曉進、陳方竟🧑🦰、張夢陽、李新宇❎、金宏達、程麻、李春林🕕、閻慶生等。他們大多為“文革”後首批招收的中國現代文學專業碩士研究生🆕,其學位論文的集中發表引起學界矚目😫。
1981年,王富仁從西北大學中文系碩士研究生畢業,三年後成為魯迅研究方面的第一個博士。1985年,他的博士論文摘要《〈呐喊〉〈彷徨〉綜論》發表🤹🏻♂️,提出“回到魯迅那裏去”的口號。
同樣是1981年🦽,錢理群在師從王瑤和嚴家炎三年之後,從北大中文系研究生畢業🚃,正式開始研究魯迅;楊義從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文學系研究生畢業🛟,師從唐弢和王士菁🏄🏼♂️🤱🏼,開始系統研究魯迅。
第四代魯迅研究者在80年代後期陸續展露頭角,汪暉、吳俊、高旭東、高遠東、王彬彬、鄭家健、薛毅、皇甫積慶等人成為魯迅研究界的主力軍。
王富仁曾比較幾代魯迅研究者的不同特點:“從方法論的角度講來,我們的爺爺輩和叔叔輩重視的是這種主義和那種主義,我們重視的則是在各種主義背後的人。我們的弟弟輩和侄兒輩則成了新的主義的輸入者和提倡者,他們的文化視野更寬廣了🙅🏽♂️,但講的又是這種學說和那種學說……對於中國人的認識和感受😰,他們反而不如我們這一代人來得直接和親切,至少暫時是如此。”
王景山和林誌浩等則屬於“一代半”,他們在新中國成立前後接受了大學本科教育👆🏽,隨後就趕上各種政治運動🧚,真正能在魯迅研究中有所作為已是“文革”之後了。
王景山與魯迅的結緣,始於他的高中時代。
1940年𓀁,王景山到內遷貴陽的國立中央大學實驗學校復學讀高中,圖書館藏書極豐🧘🏼,他對文學產生了濃厚興趣,三年裏幾乎遍讀館藏中外文學名著,其中最讓他愛不釋手的就是魯迅的小說和雜文🎞。
高二時,王景山發表了第一篇雜文《為阿Q鳴冤》。自此,他開始熱衷於發文章💇🏽♂️、“管閑事”。他說🏉,魯迅就是個“好事之徒”,自己之所以愛管閑事恐怕還是受了他的影響。
1943年🧑🧒,王景山考入西南聯大外文系。大學期間,他有過一段寫雜文的高峰期,記錄下國統區人民的生存境遇和大中學生的民主運動😚。
新中國成立後🫨,他在1956年實行“雙百方針”和1957年整風期間,模仿魯迅筆法發表了《談“禁忌”》《老八路和老爺》和《“比”的種種》等幾篇針砭時弊的雜文。他說:“過去總說‘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我卻一直認為‘天下有道’才為‘庶人議’提供了有利的客觀環境🌸。”
很快,這些“愛管閑事”的雜文就給他惹來了麻煩。1957年夏,“反右”運動開始👨🏼🚒,王景山在批判會上頻繁作檢討。為了將功折罪🤓,他積極撰文參加對徐懋庸和蕭乾的批判🤜🏻,但為時已晚🍢。一年半後,已調離中國作協的王景山仍被開除黨籍📞。對於那幾篇批徐、批蕭短文🪫💒,他後來說,這是自己的一筆良心債🫲🏻。
受處分後,王景山經作家吳伯簫推薦得以在北京通州師範學校擔任中國現代文學教員🎢。他不能再寫文章了🤟,教書也是誠惶誠恐🦶、謹小慎微🤴🏻,生怕罪上加罪✡️。後來,一些畢業多年的學生告訴王景山🧟♀️,他講的魯迅作品給他們留下了生動的印象📣🧑🏿🔧。
“文革”結束後,王景山獲得平反,重新提筆💇🏽♀️。此後二十多年🧗♂️,他陸續寫成了二百來篇長短不一的雜文。他下定決心不說違心的話,絕不自欺欺人。
1987年,王景山學習了十三大報告後,撰寫了《初級階段引起的思考》,建議全民普及“魯三篇”,分別是《隨感錄二十五》《再論雷峰塔的倒掉》和《論睜了眼看》🏌🏼♂️。1996年,十四屆六中全會召開,這一年也是魯迅逝世60周年👱🏿,王景山在“魯三篇”外又加上《這個與那個》和《拿來主義》兩篇,建議各級領導特別是高級領導在百忙之中抽時間一讀。
他說:“魯迅說‘曾經闊氣的要復古🌵,正在闊氣的要維持現狀🕖,未曾闊氣的要革新’……現在好像存在‘重孔輕魯’的一股風。‘維穩’當然要借重孔子,但‘改革’則必需魯迅。”
2004年,王景山的第一部雜文集《多管閑事集》終於在擱置多年後出版,文集模仿了魯迅雜文集的編排法,除少數使用真名😒,其余多用筆名“王荊”。
其中,《魯迅與罵人》深得王瑤贊許。在這篇雜文中🌾,王景山寫道:“既不應把魯迅之罵一概捧為金科玉律,蓋棺論定,也不好把魯迅之罵統統當作冤假錯案💂🏿,而被罵者倒是一代完人,白玉無瑕🚂。研究、評論歷史人物,只應強調一條,即歷史唯物主義🧿。如舍此不取,或另附條件🧫☕️,一陣子強調‘階級鬥爭’,於是洪洞縣裏無好人,一陣子強調‘愛國主義’,於是洪洞縣裏皆聖人⚧,竊以為都不足為訓的。”
好友閻煥東贈詩一首:“坎坷人生路🧏♂️,呐喊復彷徨。多為管閑事,屢屢遭謗傷。癡情仍不改,依舊熱心腸。無負魯門教,笑面對斜陽📯。”王景山覺得,他說的是實在話🏌🏽♂️。
“心讀”魯迅
進入新世紀,魯迅研究不再有80年代的轟動效應,不僅讀者關註減少,研究隊伍也日趨分化🔋。研究思潮從“衛魯”與“非魯”之爭,到對魯迅有了全方位的觀照。
1996年,王景山出版了題名《魯迅仍然活著》的文集,意為魯迅還活在他和無數人的心中🏓。
此時🌡,魯迅研究已難有新的重大突破。很多研究者開始了對魯迅作品的“重讀”“細讀”“新解”和“新論”🌿,以細讀文本尋求突破,由此掀起了重讀魯迅作品的熱潮。
2012年1月🤸🏿,王景山所著《魯迅五書心讀》出版,對魯迅的《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和《故事新編》中的作品做了逐篇“心讀”。對於“心讀”,王景山的解釋是👭:“不要受一時一事的束縛,不拘泥難懂的細節,跳出感官的直覺而變為心靈的體察和領悟,強調聯想🤳🏼、遷移乃至玩味🚈。通過思索著魯迅的思索🤵🤾🏼,憤怒著魯迅的憤怒,達到境界的升華和精神的契合。”
《魯迅五書心讀》主要是為青少年讀者寫的。王得後在序言中說,王景山是一個執著於魯迅精神的人,與李何林一樣,總是不忘將魯迅作品向青少年普及🧝🏼。
中學語文教材中選用魯迅作品一度占到講讀課文的10%以上💁🏻♂️,是公認的重難點👷🏽♀️,社會上對教材中魯迅作品的增刪經常爭吵不休。王景山在該書後面的《“雞肋”和中學語文教學》中寫道:魯迅🖕🏿,真是說不完的魯迅。近來又出現了新一輪熱議:魯迅的文章是“雞肋”,學生認為不好學👨🏼,老師認為不好教。據說學生有三怕:一怕文言文,二怕寫作文,三怕周樹人。
他回憶了自己求學時的情景🚘🏃♂️。當時的中學國文課本裏還沒有選入魯迅的作品,他讀初中時喜歡巴金,讀高中時先是喜歡老舍🧓🏿🛼,後來則喜歡魯迅,都是課外找他們的作品來看🫡。他覺得,如果不是逐字逐句死摳的話,魯迅的文章並不是那麽難懂🧔🏻。吳伯簫主張一般的白話文是無需字詞句段地去講解的,特別是文學作品,主要是引導學生去欣賞和領會。他同意這種看法,這也是他為什麽主張“心讀”魯迅。
他還回憶,抗戰勝利後他從西南聯大外文系轉入北京大學西語系讀大四,1947年10月正逢魯迅逝世11周年🖊,他所在的北大文藝社參加主辦了紀念會👖🧑🏽🏫,會上有朗誦,有演出🐙🫄🏽,還有校內外教授的演講🚋。輔仁大學的顧隨先生是他去請來的,所作的演講讓他印象極深⛓️💥。顧隨只是繪聲繪色地朗誦了《阿Q正傳》裏阿Q到靜修庵偷蘿蔔這段,甚至用不著講解🧺,主角和配角就都活靈活現地呈現在大家眼前,讓大家感到妙趣橫生✂️。他覺得,如果中學生聽了這樣聲情並茂的朗誦🥧,肯定會急於把原文找來看,又怎麽會覺得“食之無味”呢?
《魯迅五書心讀》被王景山稱為“有生之年最後一次微薄的努力”。88歲的他引述魯迅的話表明心跡:“我們總要戰取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給後來的🧶。我們這樣的活下去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