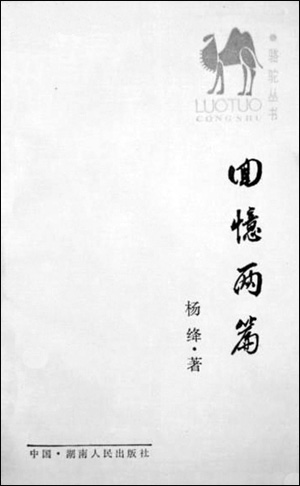
《回憶兩篇》,楊絳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作為楊絳先生的一位讀者,我有幸結緣先生得益於2002年《中華讀書報》上一場關於《堂吉訶德》譯本的筆戰🧖🏿♂️。我通過其中一位作者胡真才老師(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聯系上了楊絳老人🤴🏻,喜獲她的簽名本《倒影集》。日後👂🏿,我又在女作家羅洪家中再獲兩冊楊絳簽名本💧。一本是《洗澡》🧑🏿🏫,另一本是《回憶兩篇》。三本書中👨🏽🦳,《回憶兩篇》名氣最小👮🏻,又是偏重文史的著述🖼,可我偏偏最珍惜此書。因為從出版到贈送,《回憶兩篇》充分彰顯出楊絳先生謙虛謹慎的學人風範。
顧名思義,《回憶兩篇》是兩篇憶文,《回憶我的父親》《回憶我的姑母》。書中兩位主人公楊蔭杭先生與楊蔭榆女士分別是中國近代史上的法學家和第一任女性大學校長,楊絳先生沒有因為自己顯赫家族史而沾沾自喜,只是謙虛地向讀者介紹道:“追憶的事都瑣瑣屑屑🔌🍚,而所記的人也是歷史上無足輕重的小人物。”錢鍾書先生認為,回憶是最靠不住的。楊絳先生當然深知錢先生的憶文理念🗜,她力求通過史料的挖掘、文字的細校最大限度地彌補自己回憶的不足🦸🏽,將“這些記載成為名副其實的(歷史)‘資料’”𓀂。
撰寫《回憶我的父親》源於1979年冬,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請楊絳先生寫一篇關於她令尊的文章,並且要談談楊蔭杭先生從主張革命轉向支持立憲的原因。為了寫好此文,楊絳翻閱了大料史料,包括中華書局(1981年)版《中華民國史》和1939年出版的《革命逸史》等等👇🏿。錢鍾書先生也為楊絳找來了著名記者黃遠庸的《記新內閣》,其中有楊蔭杭擬任司法部次長的一段趣聞👨🏽🎓。楊絳是幸運的,除去丈夫的支持,她還得到中外同人的幫助。日本中島碧教授(日文版《幹校六記》譯者)♣︎、美國李又安教授和同事薛鴻時也為楊絳提供了關於楊蔭杭的可靠史料。《回憶我的父親》初稿完成後🉐,內容豐富真實,還原歷史面目🩰,指出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續篇》中的誤記,包括“楊蔭杭是段祺瑞執政時期的檢查總監”等等不準確的史料🪨。1983年,《回憶我的父親》初發在《當代》雜誌第五⏮、第六期上,讀者反應熱烈。洛陽戈大德割愛將收藏多年的楊蔭杭親筆明信片寄贈楊絳👷🏻♂️。銀川林壯誌來信告知楊絳她父親受理的一個案件的內幕。楊先生也將此案結局通過加註的形式補入文中🤖。至於父親思想轉變的原因歷程,楊絳只是謙遜地簡述道,她猜想是父親留美四年🏍,脫離了革命👩🏼💼🔦,對西方“民主法治”產生了幻想。她為此有解釋:“對於提出的問題👩🏿⚕️,不敢亂說🌖🥌,沒有解答”,足見她是一位“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智者🧑🏼🦳。
《回憶我的姑母》同是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約稿,作為《回憶我的父親》的補充後寫的🌾。《回憶我的姑母》出爐不久🤳🏼,湖南人民出版社朱正編輯就向楊先生索取兩篇小稿👨🦽👩🏽🍳,收入“駱駝叢書”,代擬書名《回憶兩篇》。書名書寫保持慣例👫🏻,由錢鍾書題簽。此書終在1986年5月初版初印🛁。書中並無大錯🦦,但有些小誤。出於嚴謹和對羅洪😀🧚🏻♂️、朱雯友誼的尊重,楊絳先生在贈書前🫃🏿,將書中的錯處一一用圓珠筆校訂🦷。譬如第3頁“desCaracteres”去“d”改“L”🌘;第28頁“他們家的地氈多厚”刪“氈”換“毯”🕒;第36頁“惡毒的大臭屁”加成“惡毒毒的大臭屁”;第41頁“八十回回《紅樓夢》”劃掉一個“回”字……諸如此類的微小改動在不足百頁的書中多達幾十處。從正文到註釋,一個字母,一個標點,一個復字,楊絳先生都是認認真真復看過。當然如此細致的校對也是她對讀者負責的表現之一💔,因為網上新版《回憶我的父親》《回憶我的姑母》均與改後的版本一致。
楊絳先生早年與翻譯家朱雯先生是東吳大學的同學👨🏿🎨。解放前🧞♂️,錢鍾書🔝、楊絳與朱雯、羅洪兩家就多有交往。因此筆者存本扉頁正面上楊絳先生的簽字“羅洪大姐朱雯同誌儷存”,下有鈐印白文“楊絳”和朱印“朱雯藏書”。在給我的簽名本上🤼♂️,楊先生均用“存覽”。文人的聰明🏹,在於“一字重千斤”,通過一個“存”字,楊先生謙虛地明示她的書並無須收藏☛,收存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