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口秀演員李誕的一句話紅了——“開心點朋友們⛱,人間不值得🍾。”
很多人喜歡這句話,似乎有種舉重若輕力量,透著李誕的“喪”式幽默。
郝景芳在一次演講裏🟠,則說起過這麽一句♿️,“在荒謬的人世間🖕🏽👈🏽,從內心獲得意義🦌。”
這句話沒有李誕那句討巧、有傳播度、更直接地戳中人群,但卻似乎更值得讓人思考。
郝景芳🎋,一個關心宇宙🗻、關心人類社會這些宏大命題的科幻作家🐂、學者🧞♂️、創業者,屢屢提及最細膩的人的“內心”。

比如去年九月份在【100Points百人計劃】的采訪裏💇🏻,她說,“所以我覺得幻想類的文學,最重要是給大家提供了一個去探討‘what if’的一個區間。在這個過程中能夠通過思考和想象的愉悅感🦪,給我們打開很多出口,在情感上走出現實的一些困局。”她將自己科幻寫作最終還是落在了個人的內心情感之上。
比如在今年1月份的一次采訪中,郝景芳談到了不同角色之間轉換時的心態,她使用了“平靜”這個詞。在每次遇到“坎”的時候🧑🦽➡️,她會去非常細微地尋找這種源頭的所在🍓,試圖解決這個問題🙈,以達到最後“內心的平靜”🪻。
在【100Points百人計劃】的這次半程回顧裏🧚🏼♀️,我們試圖用一些關鍵詞去總結與每一位嘉賓的對話🦓,“心懷宇宙,細嗅薔薇”最適合用來形容郝景芳——她以極為廣闊的視角,最終卻落在了最小個體的“內心”世界。從心出發,又回歸到心之所在。

我可以安然地接受現在的自己
“我的糾結都是圍繞著我要做什麽事情🧚🏿♂️🚳,我要成為什麽樣的人,我過去是什麽樣的人,現在做的事情👌🏼,我如何看待我自己……因為有這些懷疑和不確定,就會隨時對生活很敏感☑️🍹,對於自己的能力也很不確定👨🏼🎨。”
郝景芳的狀態,是她二十出頭的時候😮。她和每一個二十來歲的年輕人一樣👷🏻🧦,迷茫、彷徨、對自己充滿了懷疑👰🏿♂️。
大一那年,郝景芳創作了《生於一九八四》,據說,這部作品的創作初衷來源於郝景芳的困惑,“如果一切都是外界🧑🏿,如果沒有任何一個想法是我自己的🕺🏻,那我還有自由可言嗎?”
郝景芳一直保持著強烈地自省🫃🏼。初中時在語文老師的引導下👩🏽⚕️,讀詩詞💕,談俄羅斯文學🙅🏻♀️,寫周記🤕。那個時候,是她第一次在人生裏頭發現有“我”這樣的存在。從發現“我”,到懷疑“我”⬜️,再到之後關心每一個“我”,這或許也是郝景芳在之後關心更宏大的議題時,依然保持對個體的悲憫。
如今的有著多重身份的她,在各種身份之間自若轉換👨🚒。她已經沒有了年少的迷茫和自我懷疑👨👨👧👧🙍🏿,她說👩🏿🎓,最重要的是😥,我可以安然地接受現在的自己🧑🏻🎨。
“接受自己”的過程裏,女兒給了郝景芳很大的影響。她發現女兒在三四個月的時候👶🏼,對一切開始感興趣,開始心無旁騖地註視和探索身邊的新鮮事物。女兒這種對世界專註的目光,讓她意識到人在成長中👸🏿,一點一點將這種好奇與專註的眼神搞丟。

失去這種純粹的註視自然帶來一系列的焦慮。做一切事情都是為了什麽,為了提高效率,為了達到目標,為了未來某個還為到來的東西🦹🏽♀️。一切的註視都不是為了註視本身🧔♂️。
李開復在郝景芳2017年11月的新書《人之彼岸》的序言《科幻作家永遠是最前衛的思考者》裏寫到,“景芳的一番話讓我深有同感。她說👩✈️,每一個孩子都天生有好奇心,有創造力👩🏼🦲,有各種奇思妙想🥼,對這個世界充滿了愛。”
讓郝景芳能夠說出“我可以安然地接受現在的自己”這樣的話的原因🧖♂️,或許就是來自她從孩童身上重新獲得的純粹的註視與純粹的愛的力量𓀃。她從心出發,在焦慮的時代安然自若🟩。

如果做一件事情可以改變世界🔭?
二十歲出頭的時候,郝景芳也感性過。
她去校外蹭講座🚶,結束後跑去問教授,為什麽中國不能像外國那樣做好垃圾分類?我們明明可以如何如何🙋♀️?
教授說,小姑娘🌘,你知道中國有多少人在做垃圾處理嗎?沒有和她繼續糾纏下去。
郝景芳回去後,查了大量國內外的資料,才發現有一群人靠著垃圾為生。她開始重新思索不平等的問題和問題背後各種錯綜復雜的問題。

這種思維方式的轉變影響著郝景芳之後的專業選擇和寫作。22歲的她盯著美國收入分配曲線🧎♂️,想著用黑體分布或波爾茲曼分布去擬合,去證明某種普適性🦿。這種聯系與思考讓她最終決定轉入經濟系🧛🏽,從經濟學中研究不平等的根源。
“不平等”是漫長的歷史🦝。郝景芳從高中時轉入北京,質問同學關於教育資源的不平等,到二十歲質問教授後發現的垃圾問題背後的不平等,再到轉入經濟學後研究中發現的王朝經濟史裏的不平等,她一點點去觸碰不平等的根源。
在今年達沃斯論壇結束後的一次采訪裏,記者問她🧑🏽🍳,“如果你做一件事情可以改變世界👚,你覺得是什麽事情🚯🧏🏼?”,郝景芳說,“我希望能夠瞬間給所有貧困地區的孩子建很好的學校🌦🛜,能夠給他們很多的書、很多的圖書館,很多的玩具、很多的資源。”
她這一次沒有說模糊的不平等問題👶👳🏿,而是用最直白的句子👨🏽,聊最簡單的行為👩🏻🦼🧻,說出她最樸素的願望。她知道人類在與不平等的戰爭裏輸的體無完膚,但她依然願意去保留自己初心裏對平等世界的追求。

我想追尋的是人群縫隙裏的光
郝景芳說她常常不滿意在閱讀中遇到的那些將人性描寫為純粹是“對生理欲望、物質利益🦽、權力和名聲追逐的動物,似乎愛也只是生物繁殖的掩飾”,在百人計劃采訪中談到名校、學區房時💜,她也直言,“我先生是北大畢業的,我是清華畢業的,我們兩個人都覺得孩子不上清華北大無所謂👴🏽,真的上了清華北大也不過如此。我們是真真正正這麽想的。我會覺得其實對於未來時代而言,這些真正長在一個人身上的能力會比一紙學歷重要的多。”
她所做的童行計劃共享教育,也正是出於這樣的考慮🙎🏿♀️。她說她常常想尋找那些被理論所遺漏的東西、人群縫隙中的光🔳,與此同時,她又稱為這道光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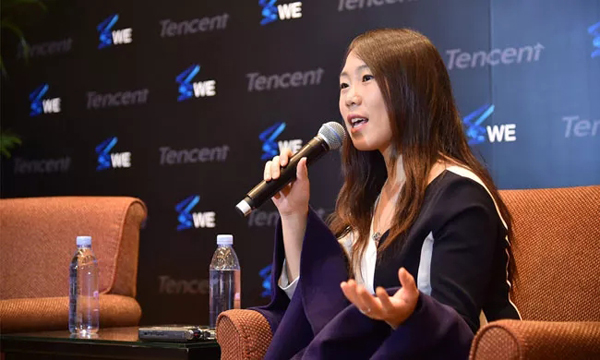
霍金去世那天,她發了一條微博,講述了在達沃斯論壇上認識的攝影師Platon Antoniou講述的關於霍金的一則故事:
“Platon去給霍金拍照的時候🧘🏻♀️,霍金的精神狀態並不好🙋🏻,眼皮一直睜不開的狀態,他的圍巾下面全是針眼,每天都需要註射多次針劑,以維持眼睛下面僅有的一小塊活躍肌肉活躍🧛♀️。就連這僅有的一小塊肌肉,也在慢慢萎縮中。
Platon快要離去的時候⛹🏽♂️,問霍金:“您能不能再給我一個詞,表明一下您想對這個世界說的話?”
他的護士說🧫:“對不起🙎🏿♀️,攝影師先生,霍金先生已經很累了🛝,他恐怕完成不了了🚓💁🏽♀️。另外,他眼睛下面的肌肉也在萎縮⚠,最近經常出錯🧏🏼♀️💁🏻♀️,可能他也做不到🍋。”
Platon正在收拾東西想走的時候,突然聽見屏幕上光標的聲音👩🏼✈️,他和護士都停下來看,看到霍金靠眼睛下面那一小塊肌肉指揮的光標在移動,最後停留在w上面。
護士還是說:“不好意思🤽🏻♂️,霍金先生最近打字經常不受控製,有的時候打出來的字是沒意義的。”
Platon正在猶豫💁🏽♂️🚴🏿,光標又動了。第二次🖕🏻,停留在o上面。過了一會兒,光標又動了。最後停留在w上面🧏🏼♀️。
wow🤘🏿。
霍金對這個世界發出的詞是驚嘆🚎。
Platon說,這樣一個全身都無法行動的人🙍🏿♂️,內心中對於整個宇宙的感覺是驚嘆,像孩子一樣發出wow♖。他的心是自由的。”
霍金對這個世界想說的話🥲,就像蹣跚學步時的嬰孩,對於世界的一切,都會發出“wow”的驚嘆。

以赤子之心從心去出發
如今的郝景芳,不再會去沖動地跑上講臺質問教授“為什麽我們不做些什麽”🐔,而是用一顆依然溫暖而緘默的初心🤵🏽♂️,去做一些事情。她從未如此深刻地認識到世界的“不平等”,也從未放棄對人性之光的追尋,和那一聲“wow”的尊敬💴。
她從來沒有阻止自己以一個作家的身份與這個世界發生關系🕢,她也不止一次試圖以獨特的風格作為個體存在🚈,於是她不斷給予了好奇心,不斷重新開始,不斷克服這種重新開始背後的可怕;作為一個更加進步更加文明的獨立女性👩🏽🍼🧑🦲,她太知道追逐路上的自由感意味著什麽,但她最終也決定了🙎,要保護自己對這個世界的好奇與堅定😠,從心去出發🧙🏼♂️。
從心出發,安然自若,感謝與【100Points百人計劃】同行的郝景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