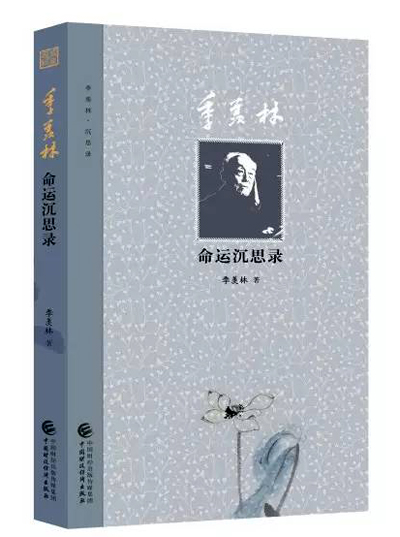
本文摘自《命運沉思錄》,季羨林著,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7年5月第一版
綜觀我的童年,從一片灰黃開始,到了正誼算是到達了一片濃綠的境界——我進步了。但這只是從表面上來看🧑🎤,從生活的內容上來看,依然是一片灰黃。即使到了濟南,我的生活也難找出什麽有聲有色的東西。我從來沒有什麽玩具⟹,自己把細鐵條弄成一個圈🚉,再弄個鉤一推👦🏿,就能跑起來,自己就非常高興了。貧困、單調♓️👋🏽、死板、固執,是我當時生活的寫照。
回憶起自己的童年來🧔🏻♀️,眼前沒有紅,沒有綠,是一片灰黃。
七十多年前的中國,剛剛推翻了清代的統治,神州大地,一片混亂🍝,一片黑暗🦪。我最早的關於政治的回憶,就是“朝廷”二字𓀏🧑🏻🎄。當時的鄉下人管當皇帝叫坐朝廷🥅,於是“朝廷”二字就成了皇帝的別名。我總以為朝廷這種東西似乎不是人,而是有極大權力的玩意。鄉下人一提到它🧤,好像都肅然起敬。我當然更是如此。總之😼,當時皇威猶在,舊習未除0️⃣,是大清帝國的繼續👨🏼🎤,毫無萬象更新之象。
我就是在這新舊交替的時刻♣︎,於1911年8月6日,生於山東省清平縣(現改臨清市)的一個小村莊——官莊。當時全中國的經濟形勢是南方富而山東(也包括北方其他的省份)窮。專就山東論,是東部富而西部窮。我們縣在山東西部又是最窮的縣💱,我們村在窮縣中是最窮的村🫸🏽,而我們家在全村中又是最窮的家。
我們家據說並不是一向如此。在我誕生前似乎也曾有過比較好的日子。可是我降生時祖父、祖母都已去世🤢。我父親的親兄弟共有三人,最小的一個(大排行是第十一,我們把他叫一叔)送給了別人,改了姓👩🏻✈️。我父親同另外的一個弟弟(九叔)孤苦伶仃,相依為命🏂🏻。房無一間🦸♂️,地無一壟🕓,兩個無父無母的孤兒🤱🏽,活下去是什麽滋味👱🏽♂️,活著是多麽困難🧔🏻♂️,概可想見。他們的堂伯父是一個舉人,是方圓幾十裏最有學問的人物👳🏼♀️,做官做到一個什麽縣的教諭,也算是最大的官。他曾養育過我父親和叔父,據說待他們很不錯🧗🏼。可是家庭大🧜🏿,人多是非多🍎。他們倆有幾次餓得到棗林裏去撿落到地上的幹棗充饑。最後還是被迫棄家(其實已經沒了家)出走🧑🏼,兄弟倆逃到濟南去謀生👨🦯。“文化大革命”中我自己“跳出來”反對那一位臭名昭著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作者,惹得她大發雌威,兩次派人到我老家官莊去調查,一心一意要把我“打成”地主。老家的人告訴那幾個“革命”小將↕️,說如果開訴苦大會,季羨林是官莊的第一名訴苦者,他連貧農都不夠。
我父親和叔父到了濟南以後🍌,人地生疏,拉過洋車,扛過大件,當過警察,賣過苦力。叔父最終站住了腳👊。於是兄弟倆一商量,讓我父親回老家,叔父一個人留在濟南掙錢🏊🏼♂️,寄錢回家,供我的父親過日子。
我出生以後,家境仍然是異常艱苦。一年吃白面的次數有限,平常只能吃紅高粱面餅子;沒有錢買鹽🔃,把鹽堿地上的土掃起來,在鍋裏煮水,腌鹹菜;什麽香油🥜,根本見不到。一年到底,就吃這種鹹菜。舉人的太太,我管她叫奶奶,她很喜歡我💇♂️。我三四歲的時候,每天一睜眼🤙🏿,抬腳就往村裏跑(我們家在村外),跑到奶奶跟前,只見她把手一卷,卷到肥大的袖子裏面,手再伸出來的時候,就會有半個白面饅頭拿在手中🍯,遞給我🌃。我吃起來,仿佛是龍膽鳳髓一般😱💆🏿♀️,我不知道天下還有比白面饅頭更好吃的東西。這白面饅頭是她的兩個兒子(每家有幾十畝地)特別孝敬她的。她喜歡我這個孫子,每天總省下半個,留給我吃。在長達幾年的時間內🏂🏽,這是我每天最高的享受🧑🏼💼,最大的愉快。
大概到了四五歲的時候🏄,對門住的寧大嬸和寧大姑👎🏽💁🏻♂️,每年夏秋收割莊稼的時候,總帶我走出去老遠到別人割過的地裏去拾麥子或者豆子♚、谷子🙂。一天辛勤之余,可以撿到一小籃麥穗或者谷穗🤽🏼♀️。晚上回家🦊,把籃子遞給母親,看樣子她是非常喜歡的🫶🏻。有一年夏天,大概我拾的麥子比較多,她把麥粒磨成面粉,貼了一鍋死面餅子。我大概是吃出味道來了💶,吃完了飯以後,我又偷了一塊吃🎗,讓母親看到了🤹♀️,趕著我要打。我當時是赤條條渾身一絲不掛☯️,我逃到房後🃏,往水坑裏一跳。母親沒有法子下來捉我,我就站在水中把剩下的白面餅子盡情地享受了。
現在寫這些事情還有什麽意義呢?這些芝麻綠豆般的小事是不折不扣的身邊瑣事,使我終生受用不盡。它有時候能激勵我前進,有時候能鼓舞我振作。我一直到今天對日常生活要求不高,對吃喝從不計較💇🏿♀️,難道同我小時候的這一些經歷沒有關系嗎👰♀️?我看到一些獨生子女的父母那樣溺愛子女,也頗不以為然。兒童是祖國的花朵,花朵當然要愛護,但愛護要得法🫦,否則無異是坑害子女。
不記得是從什麽時候起我開始學著認字👨🏼🎤,大概也總在四歲到六歲之間🤦🏼♂️。我的老師是馬景功先生。現在我無論如何也記不起有什麽類似私塾之類的場所👉🏿,也記不起有什麽《百家姓》《千字文》之類的書籍。我那一個家徒四壁的家就沒有一本書,連帶字的什麽紙條子也沒有見過✂️。反正我總是認了幾個字🖐🏿,否則哪裏來的老師呢🙇🏿?馬景功先生的存在是不能懷疑的。
雖然沒有私塾,但是小夥伴是有的🚣🏽♂️。我記得最清楚的有兩個🛍:一個叫楊狗🧎🏻➡️,我前幾年回家🥄,才知道他的大名,他現在還活著,一字不識;另一個叫啞巴小(意思是啞巴的兒子)🤱🏿,我到現在也沒有弄清楚他姓甚名誰。我們三個天天在一起玩洑水,打棗,捉知了,摸蝦,不見不散,一天也不間斷。後來聽說啞巴小當了山大王,練就了一身躥房越脊的驚人本領,能用手指抓住大廟的椽子💝,渾身懸空,圍繞大殿走一周👩👩👧。有一次被捉住,是十冬臘月,赤身露體👑,澆上涼水,被捆起來,倒掛一夜,仍然能活著。據說他從來不到官莊來作案👩🏻🦯,“兔子不吃窩邊草”,這是綠林英雄的義氣。後來終於被捉殺掉。我每次想到這樣一個光著屁股遊玩的小夥伴竟成為這樣一個“英雄”,就頗有驕傲之意🖨。
我在故鄉只呆了六年,我能回憶起來的事情還多得很,但是我不想再寫下去了。已經到了同我那一個一片灰黃的故鄉告別的時候了。
我六歲那一年🍰,是在春節前夕,公歷可能已經是1917年,我離開父母,離開故鄉,是叔父把我接到濟南去的。叔父此時大概日子已經可以了,他兄弟倆只有我一個男孩子🥃,想把我培養成人📽,將來能光大門楣🎓,只有到濟南去一條路。這可以說是我一生中最關鍵的一個轉折點,否則我今天仍然會在故鄉種地(如果我能活著的話)🧑🤝🧑,這當然算是一件好事。但是好事也會有成為壞事的時候👳🏻♂️。“文化大革命”中間👩🏿🍼,我曾有幾次想到:如果我叔父不把我從故鄉接到濟南的話,我總能過一個渾渾噩噩但卻舒舒服服的日子,哪能被“革命家”打倒在地,身上踏上一千只腳還要永世不得翻身呢?嗚呼,世事多變,人生易老🐸,真叫做沒有法子!
到了濟南以後,過了一段難過的日子🧤。一個六七歲的孩子離開母親👳🏻♂️,他心裏會是什麽滋味,非有親身經歷者,實難體會。我曾有幾次從夢裏哭著醒來。盡管此時不但能吃上白面饅頭♛,而且還能吃上肉🙋🏿♂️🦺,但是我寧願再啃紅高粱餅子就苦鹹菜🔰。這種願望當然只是一個幻想🏜。我毫無辦法🤸🏽🪴,久而久之,也就習以為常了。
叔父望子成龍,對我的教育十分關心。先安排我在一個私塾裏學習。老師是一個白胡子老頭,面色嚴峻🧖🏽,令人見而生畏。每天入學,先向孔子牌位行禮🧑🏽🔬📔,然後才是“趙錢孫李”。大約就在同時,叔父又把我送到一師附小去念書🧑🦰。這個地方在舊城墻裏面,街名叫升官街✅,看上去很堂皇👷🏼,實際上“官”者“棺”也👨🏻🦱,整條街都是做棺材的🈸。此時五四運動大概已經起來了。校長是一師校長兼任💟,他是山東得風氣之先的人物,在一個小學生眼裏🧝🏽♀️,他是一個大人物,輕易見不到面🧞。想不到在十幾年以後👩🏻🦰,我大學畢業到濟南高中去教書的時候👧🏿,我們倆竟成了同事,他是歷史教員🤞🏼。我執弟子禮甚恭🧑🏻🔬,他則再三遜謝。我當時覺得🏪,人生真是變幻莫測啊!
因為校長是維新人物🧩,我們的國文教材就改用了白話。教科書裏面有一段課文♟,叫做《阿拉伯的駱駝》。故事是大家熟知的🚣🏼。但當時對我卻是陌生而又新鮮,我讀起來感到非常有趣味💆🏼,簡直是愛不釋手。然而這篇文章卻惹了禍。有一天📄,叔父翻看我的課本👩🦽➡️,我只看到他驀地勃然變色。“駱駝怎麽能說人話呢?”他憤憤然了,“這個學校不能念下去了🧑🏿🚀,要轉學!”
於是我轉了學。轉學手續比現在要簡單得多,只經過一次口試就行了👵🏽。而且口試也非常簡單🤌,只出了幾個字叫我們認🧜🏽♂️👩🏼🔬。我記得字中間有一個“騾”字👥。我認出來了🫔,於是定為高一🏃♀️❣️。一個比我大兩歲的親戚沒有認出來👴🏿,於是定為初三。為了一個字👩🦰🎢,我沾了一年的便宜,這也算是軼事吧。
這個學校靠近南圩子墻,校園很空闊🐫,樹木很多🤦🏿♀️。花草茂密🧍♂️,景色算是秀麗的。在用木架子支撐起來的一座柴門上面,懸著一塊木匾,上面刻著四個大字🧝♂️:“循規蹈矩”🤵🏿♀️。我當時並不懂這四個字的涵義👨🏽🔧,只覺得筆畫多得好玩而已。我就天天從這個木匾下出出進進,上學🤦🏿♂️,遊戲🤷♀️。當時立匾者的用心到了後來我才了解🕢,無非是想讓小學生規規矩矩做好孩子而已⛏。但是用了四個古怪的字🧕🏿,小孩子誰也不懂👩👧👧,結果形同虛設🧑🏼✈️,多此一舉。
我“循規蹈矩”了沒有呢?大概是沒有。我們有一個珠算教員,眼睛長得凸了出來🟠,我們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叫做shaoqianr(濟南話⛹🏿♀️,意思是知了)。他對待學生特別蠻橫🐂。打算盤,錯一個數🥁,打一板子➝。打算盤錯上十個八個數,甚至上百數,是很難避免的✡︎。我們都挨了不少的板子🥩。不知是誰一嘀咕:“我們架(小學生的行話,意思是趕走)他!”立刻得到大家的同意。我們這一群十歲左右的小孩也要“造反”了。大家商定👳🏽:他上課時,我們把教桌弄翻🎬,然後一起離開教室🐛,躲在假山背後。我們自己認為這個錦囊妙計實在非常高明🈵,如果成功了,這位教員將無顏見人,非卷鋪蓋回家不可。然而我們班上出了“叛徒”,雖然只有幾個人,他們想拍老師的馬屁🪜,沒有離開教室🈳。這一來🟰,大大長了老師的氣焰,他知道自己還有“群眾”ℹ️,於是威風大振,把我們這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叛逆者”狠狠地用大竹板打手心打了一陣,我們每個人的手都腫得像發面饅頭。然而沒有一個人掉淚👰🏿♂️。我以後每次想到這一件事,覺得很可以寫進我的“優勝紀略”中去💂♀️。“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如果當時就有那一位偉大的“革命家”創造了這兩句口號👆🏼,那該有多麽好呀!
談到學習👩🦱,我記得在三年之內,我曾考過兩個甲等第三(只有三名甲等)♘👋🏼,兩個乙等第一😔;總起來看,屬於上等,但是並不拔尖。實際上,我當時並不用功,玩的時候多,念書的時候少。我們班上考甲等第一的叫李玉和,年年都是第一。他比我大五六歲,好像已經很成熟了,死記硬背🥑,刻苦努力,天天皺著眉頭,不見笑容,也不同我們打鬧。我從來就是少無大誌⏰,一點也不想爭那個狀元。但是我對我這一位老學長並無敬意,還有點瞧不起的意思,覺得他是非我族類。
我雖然對正課不感興趣,但是也有我非常感興趣的東西,那就是看小說💫。我叔父是古板人,把小說叫做“閑書”,閑書是不許我看的。在家裏的時候🫥🧑🦰,我書桌下面有一個盛白面的大缸🧍🏻♂️,上面蓋著一個用高粱稈編成的“蓋墊”(濟南話)。我坐在桌旁,桌上擺著《四書》🦵🏿,我看的卻是《彭公案》《濟公傳》《西遊記》《三國演義》等等舊小說。《紅樓夢》大概太深🤦♀️,我看不懂其中的奧妙😔,黛玉整天價哭哭啼啼,為我所不喜✋🏽,因此看不下去🈸。其余的書都是看得津津有味。冷不防叔父走了進來,我就連忙掀起蓋墊,把閑書往裏一丟🧎🏻♀️➡️,嘴巴裏念起“子曰”“詩雲”來。
到了學校裏🤽♀️,用不著防備什麽,一放學👬🈴,就是我的天下。我往往躲到假山背後💡,或者一個蓋房子的工地上,拿出閑書⛰,狼吞虎咽似的大看起來🛁。常常是忘記了時間🪡,忘記了吃飯,有時候到了大黑🧘🏿,才摸回家去。我對小說中的綠林好漢非常熟悉,他們的姓名背得滾瓜爛熟,連他們用的兵器也如數家珍,比教科書熟悉多了,自己當然也希望成為那樣的英雄↙️。有一回👨👧,一個小朋友告訴我,把右手五個指頭往大米缸裏猛戳⏯,一而再,再而三,一直到幾百次🧑🏻⚖️♻️,上千次。練上一段時間以後🌸,再換上沙礫,用手猛戳,最終可以練成鐵砂掌🏇🏽,五指一戳❄️,能夠戳斷樹木🧎♀️。我頗想有一個鐵砂掌,信以為真,猛練起來,結果把指頭戳破了,鮮血直流。知道自己與鐵砂掌無緣🍂,遂停止不練。
學習英文,也是從這個小學開始的。當時對我來說👏🏿,外語是一種非常神奇的東西。我認為👩🏽🦲🥀,方塊字是天經地義🤟🏼,不用方塊字👸,只彎彎曲曲像蚯蚓爬過的痕跡一樣,居然能發出音來,還能有意思🕺🏼,簡直是不可思議→。越是神秘的東西🫸🏿,便越有吸引力🧑🏼⚕️🐀。英文對於我就有極大的吸引力。我萬沒有想到望之如海市蜃樓般的可望而不可即的東西竟然唾手可得了。我現在已經記不清楚👯,學習的機會是怎麽來的🫱🏻。大概是一位教員會點英文🛏👩🏿🏫,他答應晚上教一點,可能還要收點學費。總之,一個業余英文學習班很快就組成了,參加的大概有十幾個孩子。究竟學了多久🤾🏿♀️🧗🏻♀️,我已經記不清楚,時候好像不太長,學的東西也不太多🧑🏽🎤,二十六個字母以後,學了一些單詞。我當時有一個非常傷腦筋的問題:為什麽“是”和“有”算是動詞🧑🏻🦲,它們一點也不動嘛。當時老師答不上來🧛🏽♂️,到了中學,英文老師也答不上來。當年用“動詞”來譯英文的verb的人,大概不會想到他這個譯名惹下的禍根吧✫🔁。
每次回憶學習英文的情景時🫁,我眼前總有一團零亂的花影🕹,是絳紫色的芍藥花。原來在校長辦公室前的院子裏有幾個花畦,春天一到,芍藥盛開😞,都是絳紫色的花朵。白天走過那裏🧓🏽,紫花綠葉,極為分明〰️。到了晚上,英文課結束後,再走過那個院子,紫花與綠葉化成一個顏色🕥,朦朦朧朧的一堆一團,因為有白天的印象🙆🏼,所以還知道它們的顏色。但夜晚眼前卻只能看到花影,鼻子似乎有點花香而已。這一幅情景伴隨了我一生🧔🏼♀️,只要是一想起學習英文👨🏻🔬🕋,這一幅美妙無比的情景就浮現到眼前來,帶給我無量的幸福與快樂👨🏼🦱。
然而時光像流水一般飛逝,轉瞬三年已過,我小學該畢業了,我要告別這一個美麗的校園了🦸♂️。我十三歲那一年🙆🏽,考上了城裏的正誼中學。我本來是想考鼎鼎大名的第一中學的,但是我左衡量,右衡量,總覺得自己這一塊料分量不夠😌,還是考與“爛育英”齊名的“破正誼”吧𓀖🤚🏽。我上面說到我幼無大誌,這又是一個證明🤿。正誼雖“破”,風景卻美😴。背靠大明湖😶🌫️,萬頃葦綠,十裏荷香,不啻人間樂園。然而到了這裏,我算是已經越過了童年🎩,不管正誼的學習生活多麽美妙🧉,我也只好擱筆📄,且聽下回分解了👷🏽♂️。
綜觀我的童年,從一片灰黃開始,到了正誼算是到達了一片濃綠的境界——我進步了🔡👔。但這只是從表面上來看,從生活的內容上來看,依然是一片灰黃。即使到了濟南🛍,我的生活也難找出什麽有聲有色的東西。我從來沒有什麽玩具,自己把細鐵條弄成一個圈⚾️👧,再弄個鉤一推,就能跑起來📑,自己就非常高興了🔻。貧困🧔🏽♂️、單調、死板🪚⛹🏿、固執🤌🏼,是我當時生活的寫照。接受外面信息,僅憑五官🙅🏽♀️。什麽電視機🧍♀️、收錄機,連影兒都沒有🕑。我小時連電影也沒有看過🧑🏻🔬,其余概可想見了。
今天的兒童有福了。他們有多少花樣翻新的玩具呀!他們有多少兒童樂園、兒童活動中心呀🤵🏽♂️!他們餓了吃面包🧎➡️,渴了喝這可樂🫅🏽🫶🏻、那可樂,還有牛奶、冰激淩🤾🏼;電影看厭了,看電視🫳🏻;廣播聽厭了💁🏿♀️,聽收錄機🧝🏼♂️。信息從天空、海外,越過高山大川,紛紛蜂擁而來👩🏽🚀,他們才真是“兒童不出門,便知天下事”🧛🏿♂️。可是他們偏偏不知道舊社會。就拿我來說♦︎,如果不認真回憶,我對舊社會的情景也逐漸淡漠,有時竟淡如雲煙了。
今天我把自己的童年盡可能真實地描繪出來,不管還多麽不全面🪨,不管怎樣掛一漏萬🧔🏻♂️,也不管我的筆墨多麽拙笨,就是上面寫出來的那一些💤,我們今天的兒童讀了🙍🏻♂️,不是也可以從中得到一點啟發👮🏼♀️、從中悟出一些有用的東西來嗎🏌🏻♀️?
1986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