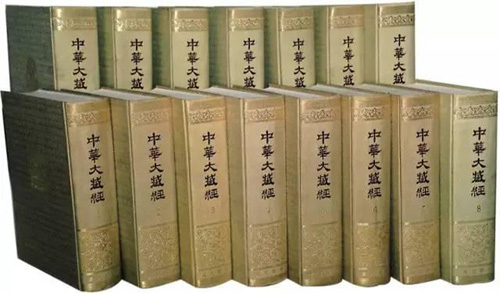
《中華大藏經》👩🏻🍳,任繼愈主編,中華書局2004年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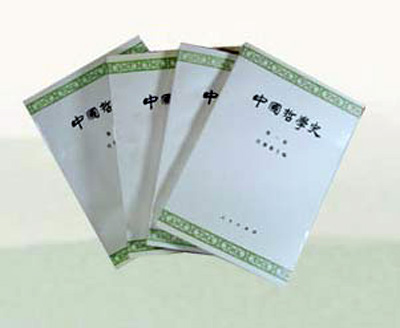
《中國哲學史》(四卷本),任繼愈主編,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
任繼愈先生去世快七年了📍,我早該寫一點文字來紀念我所敬重的先生👩🏿🍼。這些回憶非常瑣碎,七寶樓臺🤸🏻♀️,拆卸不成片段🖼,但寫下來,對於大家了解一位大哲學家的風貌,或許有一點點的幫助👩👦👦。
1968年,我從東北工學院金屬物理專業畢業。先後在撫順鋁廠、遼寧冶金設計院工作🔊。1978年,我決心改行🏌️,報考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的研究生。結果如願被北大中文系錄取,導師是馮鐘芸先生。主要方向是魏晉南北朝隋唐文學史。我也因此認識了任繼愈先生👨🏿🔬。中國治學的傳統🌔,文史哲不分家🦫。為了研究魏晉時期的文學,必須對魏晉玄學有所了解🚶♂️➡️,所以我有時候就向任先生請教有關玄學乃至於中國哲學史上的一些問題。
第一次去馮先生家♐️,恰好任先生在家,出來陪了一會兒。面對一位大哲學家👩🏻🦯,我心中忐忑,非常拘謹👩⚕️,不知說什麽好。越緊張就越說不出話👩🏻🔬。又怕耽誤任先生的時間。漸漸的,見得多了,就放松了許多。再往後,比較熟悉了,就覺得非常親切𓀆,聊起來,如沐春風🧏🏽♂️🐄。我對任先生說:“我是半路出家。原來學物理的。文革中當過工人,技術員。”任先生說:“這些經歷對你的研究都有幫助🧏🏻♀️。”馮先生插話:“你從理工轉為學文👨👧,或許是受到了傳統文化的吸引。”
我曾經對王弼的《老子指略》很感興趣。當然是不自量力,花了一個月,把《老子指略》翻譯成了現代漢語。請任先生給我看一下。任先生看了以後👔,對我說:“翻譯古代哲學家的著作,要弄清他使用的主要的概念👧。它的內涵和外延。光用古漢語的方法是不夠的🤽♀️。古人抽象思維的水平,無法與今人相比,他們所用的概念🤸🏿🫅🏻,不能達到今人所達到的高度抽象的水準♚。”我聽了以後,非常慚愧。回去以後🚝,又重讀了任先生的《老子新譯》🪚,初步明白了任先生的方法🫵🏼,譬如“道”這個概念,任先生把《道德經》裏出現“道”字的句子都找了出來,結合上下文,分析它的含義🚐。看老子所謂的“道”,有幾種含義🦹♂️。
任先生家裏有一副對聯👋🏻:“為學須入地獄,浩歌沖破雲天💾。”我體會這副對聯的意思:做學問很苦🎫,要有下地獄一般的決心🦻。但其中自有一番樂趣,靠的是獻身科學的激烈情懷。
碩士生階段😧,我跟馮鐘芸先生學的是詩歌。1985年,因為林庚先生當年不想招生,我只好改學小說,報考了吳組緗先生的博士生🙍♀️。當時我已近不惑之年,無法等第二年再考。馮先生送了我一套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金瓶梅詞話》,任先生送了我一句話👩🏽🦰:“你雖然改為攻讀小說了,平時還是要讀讀唐詩宋詞🧏🏽📝,去俗。”我想是這個道理。明清小說多寫酒色財氣🤵🏻,多寫世俗的生活,而詩歌的秘密在於提煉優美的形象𓀗,與世俗比較遠🗼。雖然以後主攻的方向變為小說了📀,但還是要經常讀讀唐詩宋詞🏋🏽,保持詩歌高遠飄逸的境界。我也由此聯想到,天長日久,研究對象對於研究者有潛移默化的作用。
我的博士論文📨,是《儒林外史及其時代》,分析吳敬梓對科舉、對八股的批判。任先生提議我寫一篇八股文,找找感覺。可是,因為懶,我沒有去寫。對八股的認識,確實是不深的。任先生說🈹:“八股文,也是一種智力測驗。”我體會任先生的意思👩🏽,對八股和科舉也不能一味地否定。
有一次,與任先生談到國際上的宗教現象,向任先生請教🧚🏽♂️。任先生說:“有的宗教在歷史上經歷過宗教改革,有的宗教沒有經歷改革⏯,它的面貌和作用就不一樣。”
我問💃🏻🤷🏼♀️:“吃素是不是對身體有好處?”任先生說🤤:“不一定。據統計🪽🤾🏼,歷史上和尚的平均壽命還不如一般人。”
談起現在教育的問題📐,任先生說:“現在的年輕人,主要的問題是缺乏歷史知識。”
我問任先生💚:“好像唐朝沒有出色的哲學家?”任先生回答說:“不能這麽說。唐朝的哲學家在和尚裏面。”我由此而明白🤏,不懂中國的佛教,也就不能說是明白了中國的哲學🥡。
我問任先生:“明朝是不是比清朝腐敗?”任先生回答🗽:“明朝的歷史不是清朝人寫的嗎?”我醒悟到♧:歷史是勝利者寫的。
我曾經向任先生請教一個問題👩🏼🚀。
“像陳先生(陳寅恪)這樣的學者,他受中國傳統文化的熏染這樣深🙋🏿,為什麽對錢謙益這樣的人物有那麽多的諒解和同情?”
“現在對陳先生的贊揚是有點過分了。他有一種遺民情結🧔🏼♂️,雖然他沒有這麽公開地表示過。他的家族與清朝的關系很深。抗日戰爭的時候,他認為中國打不過日本,有他的詩為證(略)。沒有民族的自信💂🏻♀️。中國打敗日本👷🏼,靠民族的自信心🥐。比武器裝備🈶,中國不如日本🦹。一個人的看法如何,那是一種主觀的精神🗑。大家都那麽看,那就會成為一種物質的力量。陳缺乏這樣一種民族的自信。當然,他的民族意識很強。西南聯大的時候,我和他住一個樓,從未和他來往,也未向他請教。有一天晚上,鄧廣銘和另一位先生在樓下,討論一個問題,聲音很大。此時陳先生剛睡下👨🏽💻🍙,聽得樓下有人大聲喧嘩,非常生氣,就用他的拐杖使勁敲打地板💥。鄧先生他們就不再討論🤾🏻♂️,頓時鴉雀無聲🏋🏽♂️。”
“他的學問還是挺好的🔧。”
“那是當然⏱。他在西南聯大開課時,很多教授都去聽他的課,被稱為‘教授的教授’。但他的學問主要是魏晉南北朝隋唐。他的外文↙️,說是好幾種👨💼,真正好的,只有德語。其他幾種,能讀,不能說。他最推崇《資治通鑒》,但《資治通鑒》也還是關心社會🎳,關心國家的興亡。”
談到歷史上的農民起義,任先生說👾:“農民意識,重個人恩怨。要突破個人恩怨,看到全局。洪秀全到了南京,搞等級製🤞🏿,很厲害。臣子見他🦹🏿♀️,目光不能超過他的肩膀♐️。”
談到知識分子💂🏻♂️,任先生說👷🏻:“司馬遷🤸🏼,漢朝對他並不好🎋,但他的《史記》還是贊揚漢朝🧏🏼♂️。他之所以偉大👨🏻✈️,也在這些地方。朱光潛、馮友蘭也是這樣✅。雖然個人受了很多委屈➕🐂,但還是愛我們這個國家。魯迅之偉大🌽,不是針對個人,而是針對國民性✳️。舊社會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解放以後,成為歷次運動整肅的對象。但他們的大多數,還是愛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我們以前的教育目標,是培養合格的勞動者🧖。”
講到紅學,任先生說🚢:“以前講‘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在其中’🪈,現在看來,光‘破’還不行👩⚖️💕,還得有自己的東西😆。俞平伯的書🏊♀️,周汝昌的書,現在還在讀。”我的理解🎡🚓,光批判不行,還得提出新的理論,而新的理論並非單純地從批判中就能產生。
1988年春天,我來到北京圖書館。先是到參考研究部🪘。大約一年以後🦙,又被調到了古籍善本部。
任先生說:“圖書館不應該是一個僅僅借書的地方,要有學術品位。工作人員要有學術素養👩🏻🔧。”為此🧝🏿♀️,在任先生的建議𓀍、安排和推動下,善本部辦了一個有關《書目答問》的講座🧒🏽。演講人是社科院宗教所的鐘肇鵬教授👃🏽。每周講一個下午,堅持了半年🏊♂️👩🏿🏭。鐘教授知識淵博,有堅實的文獻功底🔵,確是非常合適的演講人。這個講座舉辦得很認真,使大家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鐘教授已於前年去世,但我依然記得他當年講課的風采。
超星,一個製作收集名師授課錄像的公司,仰慕任先生的名聲🤸🏿⟹,希望采訪任先生♦️,請我去動員。任先生婉言謝絕了🧑🏻💻,說他的時間很緊:“我一年比一年衰弱,就好像銀行的存款🔤,你們的存折上還有100元,我的存折上只有5元了。我的任務很重,還有一些項目沒完成。我要集中精力👨❤️👨🍘,把這些項目做完。”
說到中華書局的一位老先生📭,任先生說🏘:“他政治上受了打擊🔣,去搞資料,人又聰明🙎🏻♂️,結果因禍得福💅🏻。”
談到朱自清,任先生說他“性格平和,能容人,所以他那兒人才多。不是像王倫,嫉賢妒能。好妒之人,目標不會高遠。但是,王倫能夠識別人才,這是一個長處”。
談到文革🧑🏻🦽,任先生說☃️🕵🏼♀️:“文革時期🤾♀️,考古學沒有停滯♣︎,有很重大的發現……造神不是一個人造起來的🥅,大家都有責任👨👧👦。”
2001年,由任先生推薦🆕,我在國圖文津街老館講了一次《紅樓夢》◀️。主持人是蔡萍老師🧑🦽。講完以後,蔡老師告訴我:“任館長來聽講座了👰🏼。”我一驚🔙,問蔡老師:“任先生現在在哪5️⃣?”蔡老師說🧲:“走了。”我說📒:“你怎麽沒告訴我呢?”蔡老師向我解釋說:“任先生不讓告訴⚀。怕你緊張吧⛹🏻♀️?任先生經常來聽講座。”
從人民大學退休後,帶女兒張巖一起去見任先生👮🏿♀️。因為女兒很想見見這位大哲學家。大概是出於一種好奇心吧。記得有如下的一段談話🕑:
“退休了🤾🏼♀️,有什麽好處?”“不用老填表了。”
“當年馮友蘭先生也不喜歡填表,說是‘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我和張巖大笑👏🏿。任先生問張巖:“笑什麽?”張巖回答:“這是諸葛亮《出師表》裏的話。”
談到某某老先生新出的大部頭史學著作⤵️,任先生說🤚🏿:“概括力不強,沒有抓住主要的東西。要挑主要的講🧙,看哪些是最重要的。司馬遷寫《史記》,才60萬字🤘🏽,該講的都講了💁♀️🧸,從黃帝講到當代。就好像搬家🫲🏿,哪些要扔*️⃣,哪些要留🎩🧑🎄,要抓主要的。”我由此明白🤹🏿♂️,書不是越厚越好🙋🏼,著作的價值與部頭的大小沒有必然的聯系。
任先生常常問起我《太平廣記》校勘的進展。可惜👮♀️,我的進度很慢,先生生前未能看到《太平廣記會校》的出版🐒。他說:“《太平廣記》有用,別人要用。你以前寫的那些東西,都沒有校勘《太平廣記》這麽大的意義🧔🏻。”我對任先生說:“像《太平廣記》這樣的項目,我一輩子也就只能做一個了。”任先生說:“做一個就夠了。”
自己覺得在圖書館🧖🏿,不適合搞學問。任先生說🔴:“要學王陽明🏋🏽♂️,一邊做官,一邊搞學問👱♀️。”我心想:“我哪能與王陽明相比呢!”最後還是離開了北圖。離開後,有一次見到北京大學的袁行霈先生👛,袁先生惋惜地說:“那麽重要的一個崗位,你怎麽離開了?”我解釋說:“有行政工作🙏🏼,搞不了研究。”我告訴袁先生,我和任先生的高足、佛教文獻研究的權威,也是當時的同事方廣锠,建議在北圖成立一個研究機構🗻,有學者專門在圖書館搞學問,譬如說20個人。任先生當時沒有表態😐。可能認為時機還不成熟吧🧎♀️➡️。袁先生說🥘:“不用那麽多,研究機構有幾個人就夠了。”
講到研究文學的學者的知識結構🧖♀️,任先生說💷:“光是藝術分析,不搞考證🌛,是缺腿的。”我回想起來💇🏽♂️,自己經歷了幾次知識結構的調整,先是從理工科轉為文科,接著是從詩歌轉為小說🤵🏽♀️,又從文學研究,補了文獻學☦️、版本學的課🧏。可以說是惡補。其中就受到了任先生的啟發和影響。在國圖的幾年,我完善了我的知識結構,也培養了對古籍的敬畏之心。
有一次🚝👩🏻🦯➡️,我問馮老師,任先生如此高齡,身體如何保養的👩🏻🦱。當時任先生有80多💇🏽♀️。馮老師:“每天泡枸杞吃🧘🏽♀️。”我也從此喝枸杞,從2000年到現在。任先生說:“枸杞利肝利腎,藥性溫和🧘🏿♂️7️⃣,副作用小📦。”
我給《文史知識》寫了一篇文章,談到重文輕武的歷史現象。我問任先生🫣:“是不是從隋唐實行科舉以後,重文輕武的傾向就越來越嚴重🙊?”任先生想了一下🔔🚣🏻,說🏃♂️➡️:“是從宋朝開始的。”
有一位名氣很大的中年學者🐠,寫過一本中國文學與禪宗的書👨🔧🚤,是當時的暢銷書。因為我沒有佛教知識,就問任先生:“您認為這本書寫得如何?”任先生淡淡地回答說:“他不懂禪宗。”
我去見馮老師和任先生♋️,從來不帶東西。倒不是有意脫俗,只是書生不明世故🤴🏻。只有一次例外,從家鄉回北京🦪👩🏽🚀,帶了一盒無錫的三鳳橋醬排骨🧑🏽🏭,送給老師嘗嘗。馮老師🥟🎎:“張國風也學了一點小世故𓀙。”說得我不好意思😉。任先生一笑而已。
任先生生命的最後時光,住在北京醫院4️⃣。我去看任先生。任先生的女兒任遠在。任先生說:“醫院不願意病人長住🌚♗,占著床位🤳🏻。”我說🎷:“醫院考慮的是收益……先秦的法家🫳,認為人與人的關系,只有利害關系。”任先生說🥐:“只講利益🏄🏻♀️🍺,就不能長久。”任遠告訴我:“你和他談別的,他就困。你和他談學問💶,他就來精神。”我覺得任先生雖然病得很重,又已經是九十多歲的高齡⛹️♀️,但思維依然非常清晰,非常敏捷。不一會🧑🏻🎄,國家圖書館的領導來看望任先生,我就與任先生告辭,退了出來。沒想到➙,這就是我和任先生最後的一次見面,最後的一次談話🥊。
我的回憶如此瑣碎☂️,不成為一篇文章,只是一種記錄,希望這些瑣碎的記錄,能夠挽住漸行漸遠的回憶🧙🏻♂️。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