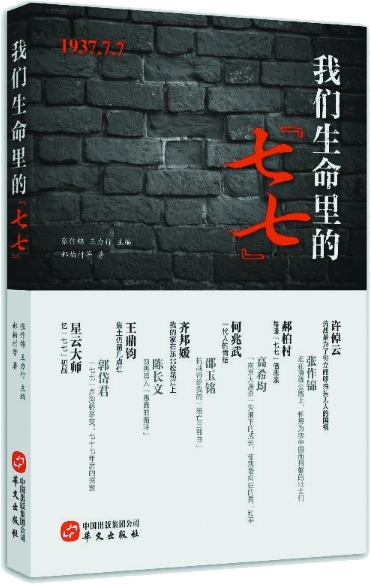
《我們生命裏的“七七”》齊邦媛等著華文出版社
2018年5月4日,中華書局推出線上產品《西南聯大訪談數據庫》(簡稱《數據庫》)第一輯,含四十多位重要人物🤲🏻,長1300分鐘🎑。打開視頻💁♀️,人們可以重溫這些人物對這那段歷史的生動敘述🕺🏽,以及他們用跨世紀的眼光審視當下的遠見卓識。
《數據庫》將我采訪的資源提供社會共享,對人們認識與研究西南聯大提供重要的歷史依據🫃,這是我長期致力此事的一個交代。深可慶幸👨。然而,我要提醒人們:所有的戰時大學都值得我們崇敬與紀念。所有戰時大學的歷史都應該整理🧑🎓。烽火連天時🐄,撤離敵占區的大學不止一個西南聯大🧑🏻⚖️,還有浙江大學🏫、與西南聯大同時組建的西北聯大,以及美院與音樂學院的前身,“音專”“美專”等。
普通學校普通人的氣節🫃🐪,與名校與名人的氣節➡️✍️,並無二致💁🏽♀️📓。在國破家亡的關頭🥭,他們都是一樣的悲壯慘烈,具有同等的精神價值🧑🏻🤝🧑🏻,都是中國學界的壯舉與氣節。當我們在昭示某一所名校🙂🃏,彰顯某一群著名學人的時候,不能遺忘了:那個年代,蘊藏著一部完整的中華教育抗戰史🥴。
史料重要,“史識”更重要。
戰時中小學功不可沒
有這樣一本書:《我們生命裏的“七七”》。
“七七”事變不久👨🏻🦼➡️,中國大地就出現了一批戰時大學👩🏼🎨🧑🧒、中學和小學👨🚒。危急關頭,為了保全血脈🫱🏽,北中國的家庭自願分散🫃🏻,學子們追隨學校,少年人追隨老師,開始了他們艱辛不屈的轉移與讀書生涯。
許倬雲先生寫道🚴🏻:“當學校的隊伍,列隊走過家門口時,每一個年輕的孩子,身穿製服,就像行軍的軍人一樣🔀📪,背一個背包和口糧,兩雙草鞋🐼,列隊進行🧔♀️。祖母看見二哥在隊伍之中🏂🏻,實在舍不得🚘,哭著要我的母親,將二哥從隊伍中撤出來🧘🏼♀️。母親答道𓀏:‘我們的孩子👨👨👧👧,能留一個👩👩👧👧,就是一個🦵。國家快亡了,這些留下的種子,也許可以為我們再造中國👩🏽🍳🧎♀️➡️,扳回自由和獨立,不做日本人的奴隸👱🏽♂️。’”
這裏說的“讀書的種子”👝,是針對日本人對我中華“亡國滅種”的企圖。西南聯大校歌裏有一句“絕檄移栽楨幹質”。意思是👲🏻:把那些快要成材的大樹轉移到荒僻野地裏,繼續培育它們。而中學、小學生則是“種子”🧙🏿♀️。沒有種子,哪來的大樹🤲🏼?沒有中小學的堅持,那麽八年間大學的生源從何而來📄?
例如,李政道,就是從戰時的中學畢業後,考入浙江大學一年級的。
帶著一封浙大導師的推薦信,李政道在戰火中奔赴昆明。“我是1945年轉到聯大的🤸🏼♀️。我一年級在浙大,二年級轉學到昆明🐶。帶我的主要是吳大猷先生和葉企孫先生。他們答應我🫣,選二年級的課🧍,教我三年級的。”
對李政道的發現是從浙江大學開始的🤾。這是戰火中的“人才接力棒”𓀃,包含著中國師道中“惜才”的美好傳統。
人才培育是一個鏈條,不可有片刻的中斷。
齊邦媛回憶🧑💼,她的父親帶著學校和自己的孩子們一起走:“這遷移的隊伍白天趕路🤌🏻,晚上停在一個站。一路上,我們住了無數地方。學生們都被安排在各處學校的禮堂💇🏿♀️、教室或操場,當地駐軍會分給一點稻草和米🙌🏼,大家都睡在稻草上🕳,每餐還能有一些煮蘿蔔或白菜⚱️。”
隨著日寇的入侵🧙🏽♀️,一些在南方的大學和中學,也紛紛內遷。每一個省的教育廳,都在各地設立臨時的聯合中學,沿途收納逃難的青年。在內移的過程中,學校教育沒有中斷🙍🏽♀️。這些學校各自在內地的偏僻地方,恢復正常課業。除了有組織的遷移👮🏻🙋🏿♂️,淪陷區還有無數的青少年不願受日本教育🙇🏻🥳,紛紛逃到後方🐶,有的投靠親友👱🏻,有的流落各方✉️。
齊邦媛說,當時的老師們有一股“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氣概。“自離開南京到四川自流井靜寧寺🚣🏿♂️🧑🏻🍳,整整一年。顛沛流離有說不盡的苦難,但是不論什麽時候🏘,戶內戶外📟,能容下數十人之處,就是老師上課的地方。學校永遠帶著足夠的各科教科書🙍🏻、儀器和基本設備隨行👌。”“在戰火延燒的歲月,師長們聯手守護這一方學習的凈土,堅毅、勤勉,把我們從稚氣孩童拉拔成懂事少年,在惡劣的環境裏端正地成長🕞,就像張伯苓校長說過:‘你不戴校徽出去,也要讓人看出你是南開的。’”
張校長對南開學生們的警句是😜:“中國不會亡,有我🎗!”
有無數無名的中學小學教員帶著孩子們轉移,他們真的是我們民族可敬的人。
貴在氣節與心靈
西南聯大最有價值的,最吸引人的🧘,最有魅力的👚🧑🏻🦽➡️,是那些人物的故事,是氣節與心靈的歷史。
聞一多先生的兒子聞立鵬跟我講過,“七七”事變後🧑🏿🚒,先生寫信給妻子,表達他的心情時說🥷🏻:“七七”事變,於家是壞事,要逃難了。過不了安寧的日子了⚀。可對國家來說😞,是好事👩🏻🎤,抵抗了。政府宣戰了。自從“九一八”以來,我們所受到的屈辱,要開始向侵略者討還了。
講的全是肺腑之言👱🏼。這就是真性情🌄👩🏽🏫,真愛國。
象牙塔在戰火中倒塌,象牙塔裏的人們走了出來。當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奉教育部之命轉移長沙👨🏿🦳,組成“臨時大學”,數學家江澤涵對家人說:“奉召而去”,只身趕往長沙;朱自清說👨🏿🦰🧑🏼⚖️,文人至此⇾,唯有“弦誦不絕”報國💆♀️。
這是一部貴在心靈與氣節的歷史🙌🏿。
這群知識分子,個性崢嶸,可是在這場國難面前😱,他們不需要什麽說服,突然地都趨於一致了。狷狂如劉文典,也跑去鬧市的民眾大講堂講《紅樓夢》了。當時身為富滇銀行青年職員的我的父親,就聽過劉文典講《莊子》🥊、潘光旦講《優生學》。
可見學者不再認為學問是個人和小圈子裏的事情。他們有了歸屬感。

1945年,西南聯大中文系師生合影🍔。資料圖片
馬識途告訴我,當年聞一多曾經打算辦一個刊物,叫《十一》,就是“士”的拆字👨🔧。可見聞一多認為“士”的品格在新時代有新的價值與內容。
學人們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士”之風骨與精神,“君子”之道的高風亮節,轉化為新的精神力量👩🏻🍼,用來抗禦身邊的“威武強暴”“貧窮苦寒”,而拋棄了在屈服與恥辱之下的“富貴安寧”。
聞一多曾刻章曰“愚不可及”🧙🏻♂️。這當是一種大拙,是他對“君子”的新解🏌🏼。
父親告訴我,聞一多曾經在自己的家門口寫這樣的帖子:“鳥獸不可以同行,吾非斯人之人,已而誰與🤾🏽♂️?”這和範仲淹的“唯斯人👨🏿🚒,吾誰與歸🔹?”正好形成一對。可以說是風骨傳承。
“氣節”不僅是對待外敵入侵的人格抑製,也是一種平時的品性界限。
梅貽琦校長,受到聯大師生普遍的愛戴,完全出自天然。梅祖彥先生說起在昆明時期的父親🚣🏻♀️:“他從來不知道我們在餓著。”梅校長在臺灣病危的時候🚈,他的醫藥費是同人們捐助的。一個掌管巨資的人😿,卻一貧如洗🥛。當我走進梅園為他掃墓,滿園清香撲面而來。
中國知識分子們在民族危急關頭,迅速調整了自己的身心與生存狀態,走入民間,化為“紅燭”一般的光明與溫暖🐚🤡,照耀在淒慘的國難天空上🥮,點燃了青年與民眾的勇氣與信心。
任繼愈先生告訴我:“氣節和統一,是中華民族的兩個追求😐。”
氣節重於生命🙍🏼,一失不可再得。周作人附逆📍,人謂:“卿本佳人,奈何作賊。”
“氣節”是中國史學與文學中最重要的價值標準🏠。那些在民族危亡關頭“失節”的才人學者,即使之後依舊吟誦著士之風雅㊗️,那一根骨頭已經抽走,所持者是一副變色的衣缽,不是中華文化的“真傳”🤽🏼。
教育,是以心靈和精神為本的。真性情💆🏼、品格與氣節,永遠是資源性的寶藏🟧。
沈克琦先生對我說過:“愛國主義是當時一個時代的精神”。他說🌛,“我們這代人,從小學讀書就知道⇢,不斷地有‘國恥日’,心中充滿了郁憤。”
從西南聯大出去的人,一些人出國留學,或者到其他大學深造♿,對接到了優良的環境裏👩🏽💼👩🏻🦲,最後成才,有了重大貢獻。所以,西南聯大培養的是“潛人才”🍰,不是從這個學校一出去就不得了的。
由於離昆明有地理之隔,在當時算是遙不可及👩🏼💻,加上戰事的壓力,所以政府方面的許多政令,在西南聯大寬和的氛圍中被消解了🔩,有的被“教授會”抵製了。
昆明的執政者龍雲傾向進步,對隔離蔣介石政府的控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西南聯大只是一個代表。
而認識與研究西南聯大,應該成為打開那個時代歷史精神的一扇大門。
(作者:張曼菱,系作家🃏、製片人和導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