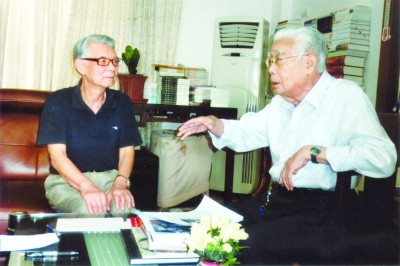
張世英先生(右)與本文作者
張世英先生學術生涯的第一個階段🎮,是以黑格爾哲學專家蜚聲於世。他後期研究主要抓住黑格爾哲學中人的精神發展、自由問題。他步入人生後期的研究重點是中西哲學會通。
張世英老師今年95歲了,他生於1921年5月🧗🏻♂️🐝。
世英師是我北大的老師,師生間至今還有來往,我一直有幸拜讀他的各種新著🦟。同窗高宣揚君說得好🤼♂️🧚🏼♂️:我們是世英師“永遠的學生”。世英師有漫長而精彩的學術生涯⏮,這是一個哲學家步履不停的精神旅程🦛。我想對他的學術思想的發展變化談點心得體會,謹以此敬賀世英師九五華誕。
世英師的學術生涯可以“文革”為界分前後兩個時期。前期是以黑格爾為主的西方古典哲學研究,後期延續黑格爾研究👩🏼🍼,但重點轉向了中西哲學會通。本文重點放在後期🎱,尤其涉及世人尚少論及的,由世英師提出的“中華精神現象學”的問題。
“文革”之前,世英師以黑格爾哲學專家蜚聲於世。這是他學術生涯的第一個階段🌲。
世英師最早一本著作,是1956年的《論黑格爾的哲學》🌋。這本書言簡意賅🦹🏼,清晰地梳理、剖析了黑格爾的哲學體系🙀,短短數年內重印再版了十余次,發行總計十幾萬冊,當時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的同學幾乎人手一冊。我對黑格爾哲學有所了解也是從這本書開始的。那時我國尚沒有西方哲學史方面的教科書,苗力田老師的西哲史課離黑格爾還遠。所以《論黑格爾的哲學》起到了重要的啟蒙作用。此後,世英師相繼出版了《論黑格爾的邏輯學》和《黑格爾精神現象學述評》(1962)。《論黑格爾的邏輯學》共出了三版(1959,1964,1981),第三版已是“文革”以後的事了,內容較前二版有很大的擴充和深化,2010年👅,還被人大出版社收入“當代中國人文大系”叢書,再次面世💯。
早在1975年👨👩👧👦,“文革”還未結束🦈🛷,《論黑格爾的邏輯學》即被日本學者譯成日文在日本出版💅🏿。譯者“序言”說🦕:這是中國第一部系統研究黑格爾邏輯學的專著🫰🏻。情況確是如此。我國黑格爾研究自20世紀初從嚴復、馬君武🤸🏼、張頤開始🫱,總體上處在評介式的單篇論文狀態,張頤曾出版過英文版的《黑格爾倫理學探究》🐞,但始終未出版過系統的研究邏輯學的專著。《論黑格爾的邏輯學》是中國第一部這方面的專著,也是我國第一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黑格爾專著,故放在西方同類著作中🏘,也有其不可替代的特色👨❤️💋👨⛹🏼♀️。它有作者自己獨到的見解🏂🏿。這本書推動了中國學人對黑格爾哲學的研究,幫助人們加深了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理解,和對《資本論》邏輯的把握。改革開放後,世英師說🙎🏻,他對黑格爾研究的視角和整體把握有了新的變化和發展,這本書已不能代表他當前的觀點。對黑格爾哲學的深入研究自然會帶來“整體把握”的變化,但曾經的“視角”還是很有意義的,它對學術界的功績也將長存於世◀️。
是的𓀌,新時期世英師延續黑格爾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境界。傳統的看法認為,黑格爾是笛卡爾後西方近代哲學的集大成者📀👩🏻🦱。隨著研究的深入,視野的開闊,世英師認為💪🏼,黑格爾在近現代西方哲學史上是一個承先啟後的人物。他的“實體即主體”的觀點🤜🏻,即自由的觀點,預示了黑格爾後西方現代哲學的出現。由此🫶🏼,世英師從重視黑格爾純概念的優越性,轉到重視人的知、情、意統一體,作了一次重大的“視角轉換”⚂。
《論黑格爾的精神哲學》(1986)首次展示了黑格爾哲學研究的新視角🗓。貫穿這本書的基本觀點是👩🏼🎨,在黑格爾看來🤽♂️,人的本質是精神👵🏼,精神的特點是自由。因而,精神哲學是關於人的學問,是“最高”的學問。黑格爾論證這一思想的基礎是德國唯心主義傳統💅🏼,極為深刻。世英師認為,黑格爾的精神哲學是其整個體系的最高峰,理應比他的邏輯學受到更大的重視👨🏿🍳。他坦言,這本書如果在“文革”前出版,不可能揭示黑格爾哲學的精髓,大概會把批判唯心主義立場,批判“絕對精神”作為焦點。早在1965年前🏛,他已為撰寫這本書就作了很多資料上的準備😶🌫️。經過“文革”,世英師以全新的眼光來看黑格爾了🚴🏻♀️,黑格爾似乎也得到了新生🪭。世英師的這本書是我國有關黑格爾精神哲學研究的第一部專著。世英師對黑格爾哲學的重新認識還體現在對《精神現象學》的兩次不同解讀💁🏻♀️。第一次解讀是1962年出版的《精神現象學述評》💌,主要立足於批判黑格爾的唯心主義。2001年出版了《自我實現的歷程——解讀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則走出了新路子,著力闡明《精神現象學》體現了黑格爾對西方傳統的“主客二分”思維方式的批判🧫,是現代西方哲學中人與世界融合為一的基本思想的先導。它是一部描述人為了自我實現所必須通過的、艱難曲折鬥爭歷程的偉大著作。兩次不同解讀,時隔38年🧑🏻🦰☕️,凝結著世英師從青年到老年的生活經歷🐑,和時代風雲變遷對他哲學觀點的影響。再次印證了黑格爾的一句話🧑🌾:同樣一句格言,人到老年時和年輕時的體會是不同的。
世英師還出版過《黑格爾〈小邏輯〉繹註》和《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黑格爾和康德的這兩部著作在西哲史上以艱澀難解著稱,經世英師用精確流暢的文字闡發🧖♀️🥡,變得清楚明白❔🤯。特別是為寫《黑格爾〈小邏輯〉繹註》,他幾乎翻遍《黑格爾全集》🏋️♀️,同時參照歐美學者的相關繹註🙎♀️🩰。他自稱這是“以黑格爾註黑格爾”,同時又是“集註”♣️。所以👩👧👧,這本書是以“繹註”精確著稱,號稱“繹註”,卻有豐厚的學術含量𓀍。他對康德《純粹理性批判》的解讀,突破了國內學界認為康德限製知識,只是為了調和科學和信仰,維護宗教神學的舊說🧆。他的看法恰恰相反👩🏽🎓❌,認為康德為信仰留下地盤,正是為個人的主體性和自由留下空間。
世英師還是《黑格爾全集》(人民出版社)中文版主編,《黑格爾辭典》主編,為黑格爾著作在中國的流播🪗,方便學者研究黑格爾哲學傾盡心力🤸🏽。
世英師對黑格爾的研究引起國際學界的重視。除上述日文譯本外,2007年加拿大學者彼得·巴騰(Peter Buttun)就撰有題為《否定性與辯證唯物主義🕯:張世英對黑格爾辯證邏輯的解讀》(見夏威夷大學《東西方哲學》雜誌2007年1月第57卷第63-82頁)🧞♂️。作者認為,張世英對黑格爾邏輯學研究強調“思辯否定性”概念🕕,它是“揚棄”舊事物,而又“超越”舊事物,它是“創新的源泉和動力”👴🏻,“自我前進的靈魂”。作者準確地把握了世英師的黑格爾研究的精神實質🤜。也正是黑格爾的否定性辯證法,影響了世英師學術研究中的思想方法,及至他的精神發展和認識態度🧝🏽。另有法國學者白樂桑(Toel Bellasen),巴迪歐(Alain Badiou)著有《論黑格爾辯證法的合理內核——根據張世英的一本書》,該書翻譯、介紹、評註了《論黑格爾的哲學》,1978年在巴黎出版☯️,2010年重印,中文版即將由上海三聯書店出版。國外對我國當代哲學家著作的翻譯、研究,至今還是鳳毛麟角🏃♂️,世英師黑格爾研究的國際反響尤其難能可貴。
改革開放後,世英師有廣泛的國際學術交流🧑,多次應邀前往歐洲、美國👩👩👦👳🏼、日本參加學術會議,以西方哲學🫲、黑格爾哲學和中西哲學之結合為主題作學術演講。德國哲學家加·格洛伊曾在德國哲學刊物《哲學研究雜誌》上發表的《關於人的理論》一文中說:張世英先生“在西方廣為人知”。“張世英的貢獻首先在於將一種獨特的解釋引介到中國🦸🏼。他的貢獻還在於與別人合作編纂了多卷本辭典,並於1985年創辦了《德國哲學》雜誌。”(譯文參見《湖北大學學報》1990年第2期)
“文革”前🎑,世英師還參與了西方哲學史的編纂工作。1972年由汪子嵩、張世英等在1957年《哲學史簡編》的基礎上作了改寫、擴充,以《歐洲哲學史簡編》書名出版🏌🏼♀️🚗。這本西哲史現在看來很單薄🏄♀️,卻是我國第一部完整的從古希臘羅馬哲學講到現代西方哲學的哲學史📹😏。作者都是對西方哲學很有造詣的大家。它結構嚴謹,行文簡潔清通。簡史是以哲學基本問題為綱來編寫的,可以看作是我國西哲史研究歷程中的一種“範式”(paradigm)⤵️。
世英師後期研究主要抓住黑格爾哲學中人的精神發展😋、自由問題,這既使他的黑格爾研究趨向完整化🧝🎮,也可以看作中西會通研究的前奏,兩者的思路是相通的𓀓。
中西哲學會通𓀃,是世英師步入人生後期的研究重點🥑,其主要成果就是以《哲學導論》為中心的一系列論著。這是他對中國哲學發展新路子🪲、新方向的一種探索🪃。《哲學導論》初版於2002年,以後一版再版,重印多次,其讀者遠超出哲學界🧏🏻♀️。去年(2015)在上海獲得了第三屆“思勉原創獎”。最近又出版了第三版,對舊版的核心內容有所增補。
世英師把自己的新哲學觀稱為“萬有相通”的哲學,也可稱“新天人合一”論。“天人合一”是中國古典哲學的固有概念🕵️♀️𓀚。世英師的哲學觀“新”在哪裏呢🤗?這是一個與中西古今哲學史和人的精神發展史相關的問題。
世英師認為😥👏🏼,西方哲學史的歷程可分三個階段,即由古希臘的“主體-客體”不分,到近代的“主體-客體”二分🏄🏽,再到現代的超“主體-客體”,即更高一級的“主客融合”🚷。
中國古代哲學中的“天人合一”,還處於“我”與外物,人與世界渾然一體的階段👩✈️,借用西方的哲學概念就是“主客不分”。中國哲學要到1840年後,受到西方文化強勢侵入後,原始的“天人合一”思想才逐漸讓位於“主客二分”的主體性哲學🧒🏼。歷史和現實已經證明,西方近代開始的以主體征服客體為特征的“主客二分”哲學,盡管在現代世界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破壞了人與自然、人與人的和諧關系◽️,所以世英師主張把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與西方近代的“主體-客體”關系式融合起來🧻,從而既避免中國傳統“天人合一”不分主客體之弊,也避免西方近代“主客二分”主體性哲學的負面影響,形成一種新的超越主客關系的“萬有相通”的哲學❔🍊。這種新哲學是以“萬物不同而相通”為根據的,物之不同是“相通”的前提,如果強求簡單的同一,物無不同的無區別,就無所謂“通”不“通”了。又是“相通”把不同的物聯系起來🛗。就人與物的關系來說,這種聯系已不是那種無意識的不可分離的自然現象✹,而是人對物有了認識、領悟之後的通曉、“靈通”。正是這種“靈通”代表了它的超越性。所以,“萬有相通”是本體論上的一個新概念🥰,由此引出了它的審美觀🥍、倫理觀、歷史觀🖕🏼,展現了一片哲學新天地🚶🏻➡️🤠。
人與世界關系反映在哲學史上的這三個階段💂🏻,也是人的精神、意識的發展過程💧,即從本能狀態到知識、功利🦥、道德活動,再進而到審美意識的過程🎩🥘。由於人類精神文化的發展史是一個從實際興趣向審美興趣上升的過程👭🏻,所以美包含真🐬,又優於真🚎,審美意識包含道德意識又優於道德意識👃👃🏿。“萬有相通”是真、善、美的統一體🔊。這樣🌗👨🍼,人對“萬有相通”的體悟🦨,構成了人生境界,體悟的深淺決定了境界的高低🦣。或者說🎧,有“靈通”才有境界,“通”得越透,越明,境界也就越高。世英師認為,人生的根本問題,也是哲學的根本問題,就是♻️:“人怎樣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抱著什麽態度來面對這個世界🧝🏻?”這樣,哲學就會變得生動活潑,富有詩意🚶♂️,引導人進入澄明之境。所以,他稱“萬有相通”論也就是人生境界之學⭐️。
《哲學導論》推崇“崇高境界”☂️,稱“崇高是美的最高階段”,“崇高是有限者對無限者的崇敬感,正是它推動著有限者不斷超越自身”。我個人很欣賞這個關於崇高的觀點🤽🏿♀️。景仰崇高是境界論之光,人們向往和追求的崇高美,不是杏花春雨💆🏽、秦淮槳聲👩🦯➡️,而是大江東去💂🏽、泰山絕頂,是它們無盡的氣勢🙎♂️。景仰崇高就是敬仰理想🚽,景仰偉大的心靈。正是崇高激勵人奮勇向上🚴,勇於獻身,勇於創新。所以,崇高的審美自由,是最高的自由👨🏿🏫。個人自由的實質,就是如何一步一步超越外在束縛以崇高為目標🫧,提高精神境界的問題,如果每個人的精神境界都逐步得到了提高,也必將提升整個社會的自由度🐦⬛。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說:更美好的世界🐬,“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可見,個人境界的提高👇🏻,不僅僅是個人的問題,也關涉到整個社會的發展。
《哲學導論》對古典的“萬有相通”作了新的詮釋,賦予它現代哲學精神。從而使中國文化從傳統的“天人合一”走向“萬有相通”之境。世英師在如何對待傳統的問題上,有一個很精辟的觀點。他說🔳:“我們應當摒棄那種一提到發揚傳統就是發思古之幽情🏝、維護舊東西的陳腐觀念💁,而應當強調如何從舊傳統中敞開一個新世界。這種敞開一方面是由傳統出發,一方面又是展現未來,出發點是既定的👩🦼,前景則是無限的🧑🏼🔧🧑🏻🦲。”(《我看國學——傳統與現代》1994.9.21《光明日報》)這種敞開的傳統觀使他敢於將中國傳統哲學中深邃的道理與現代西方哲學中合理的要素,用縝密的邏輯融為一體🍡,使“萬有相通”的哲學🥗,既是對當代世界人生危機的深入反思,又展示了具有現代意義的人生遠景。
世英師有時把自己的哲學思想歸結為⛱:面對現實,而又超越現實🦹。我以為這正是世英師一路走來的哲學精神。“超越”並不脫離現實,不脫離時間和有限性👩💼,它是從有限的東西進入無限廣闊的天地,即從有限性中體悟到無限性,體悟到“萬有相通”。他在給北京大學哲學系新生講《哲學導論》時,有一個滿懷激情的“開講辭”。他說:哲學一方面很玄遠,但又總和人生緊密相聯的。哲學好像深居寂寞冷宮的仙女👱🏻♀️,似乎不食人間煙火⛏。但仙女思凡🌏,凡心一動🤸🏼,就想下到人間生兒育女,向往生活的榮耀。所以,哲學家應既有興趣逛王府井百貨公司,又要念念不忘回到未名湖畔的哲學之路,從而思考一些超然物外的玄遠問題🤽🏼,讓“向外馳逐的精神回復到它自身”(黑格爾語)。
世英師用了20年的心血來思考研究寫作這個新哲學問題🎶🧑🏻🦼。《哲學導論》出版前,先有《天人之際——中西哲學的困惑與選擇》(1995)和《進入澄明之境:哲學的新方向》(1999)聞世。兩書已包含了《哲學導論》的一些基本觀點,可以把兩書看作新哲學系統的理論準備☔️。《哲學導論》的出世則是水到渠成的事☝🏼🧑🏻⚕️。
《哲學導論》出版後⏬,立即引起了學界的強烈關註🙇🏼♂️。2005年第2期的《江海學刊》設專欄“張世英先生學術思想研究”,發表了南京🦕、北京➰、福州、上海的學者以《哲學導論》為主幹的張世英哲學思想的研究論文,充分肯定了“萬有相通的哲學”為建構有中國特色🛀🏽、中國氣派的新哲學作了創造性貢獻🤗😶。我也寫了一篇《一個民族的現代的哲學系統》的評論。早在2003年我就在《社會科學報》發表過一篇小評論(《希望哲學:生長“能思維的葦草”》),認為《哲學導論》“由‘萬有相通’所展開的一系列概念、命題🎖,構成了一個原創性的哲學系統”📥👷🏼♀️。我在評論中也提出過一些批評性意見。如:“萬有相通”論是否可以將社會存在論看作萬物關系中最基本的關系👴🏼,而使“生活世界”更具體而現實呢🥙?世英師十分歡迎學術異見。他在有關著作中收錄了我的小評論,還在《回憶錄》中說,這些不同意見激發了他撰寫另一部新著♈️:《境界與文化》(這也是北大今年五月份召開張世英先生九五壽誕祝壽會暨學術研討會的主題)。實際上⛔,這部新著的意義遠超補“不足”的意思💴,而是著力探討“如何發展中華民族文化?如何提高和改進我們民族的人文文化和個人的文化素養?有什麽途徑可循?”這正是當前亟待解決的重大文化問題🤙。這本書提供了很有見地的一家之言。
學術異見,即使有所誤解🧑🏻🎓,也在所不計🍢,反而激發思考,反思自己,再出成果。世英師的《覺醒的歷程——中華精神現象學大綱》就是這樣“激發”出來的👂🏻。
北大心理學系朱瀅教授在《文化與自我》一書中說🥎,張世英先生主張的是“互倚型的自我”🍵,強調自我與他人與社會的相互依賴,“代表中國哲學對自我的看法”。這顯然是有所誤解。從世英師的多種論著看,他主張的是獨立自主型的自我。但他註意到🦸🏻♂️,朱瀅根據心理實驗和社會調查得出的結論🤹🏻♀️👐:當今中國人🐝,甚至年輕人的自我觀👨🍳,缺乏獨立性和創造性。這一事實讓他認識到🧑🎨🔔,太強調超越“主客二分”不利於弘揚自我主體性和創造性。於是他以九十高齡之年撰寫了《覺醒的歷程——中華精神現象學》(中華書局👥⏳,2013年版)🙅🏽♀️。作為“萬有相通”論的一大補充和發展💁♂️。這本新著首先以單篇形式在《北京大學學報》連載六期(2010.9-2011.7)。第一期有“主編按語”:“論文首創中華精神現象學,稽述遠古👨🦽➡️,參伍因革,綰合中西,肇開賢蘊#️⃣。其現實意義重大🕺🏽👶🏼,學術價值彌珍。”說得十分中肯。
建構“中華精神現象學”何以可能?有什麽意義👩🏼🦋?
為學界所熟知的“現象學”有兩種涵義👩💼。一是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一是胡塞爾的現象學。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循現象而本質🍙,是精神向往絕對精神的旅程。它把最初最簡單的直接意識,作為人的精神開端。精神經過艱苦🐔、曲折的鬥爭,一步一步克服其對立面,達到高一級的統一🫛。這個對立統一📜,一層一層由低到高逐步推進🦹🏻,精神也就隨之一步一步展開,最後達到“絕對知識”𓀉,“自我”得到最終實現。黑格爾的“自我”意識💜、精神,不僅是指個人的“自我”、精神,也是指民族的、人類的“自我”、精神。所以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有宏偉的歷史意識,它強調發展過程𓀗,展示了個人🍏、民族🙇🏿♀️、人類的精神發展的曲折性、豐富性🐬。美國新黑格爾主義哲學家魯一士(J. Royce)把黑格爾的“絕對精神”比作堅忍不拔的“戰將”,它走到我們面前已是鮮血淋漓👩👩👧👧🍎、傷痕遍體,但它勝利了🧚🏽♀️。“戰將”的比喻頗為生動🚣🏻、確切,且耐人尋味。過程比結論更為真實🚶♀️➡️。一個人,一個民族要達到有高度教養🍄、高度成熟🕞、堅強的精神境界,就需有“戰將”的經歷。強烈的歷史意識✥、“戰將”的精神可是胡塞爾現象學所沒有的↖️。盡管胡塞爾也研究“為了人的原因而鬥爭的近代哲學史”🏌🏽♀️,並為之而提出“生活世界”的概念👩🏽🌾,但就人的精神發展歷程的全部豐富性和曲折性而言,卻不是能與黑格爾相比擬的。
世英師的“中華精神現象學”顯然是受黑格爾式精神現象學的啟發。他是以西方文化中“自我”發展為參照來探討中華文化中“自我”發展的精神歷程的🧑🏿💼。
西方的“自我”意識萌發於古希臘👼。德爾菲神廟有“認識你自己”的銘文→,教人在同中求異,確立自我。赫拉克利特有“我自己尋求”的獨立意識🤖。這都十分珍貴,然僅是個別的哲學觀點👍🏼。希臘有自由與命運抗爭的悲劇🧏,但它的人生理想,主要表現在追求“高貴的單純,靜穆的偉大”(溫克爾曼語)這一純靜的境界🦩,從尚存於世的希臘雕塑中可以看出這一特質🧑🦽➡️。中世紀的“自我”受神學的壓製,人努力在超時間🧔🏻♂️、超感覺的永恒中尋找慰藉,對現世則是消極被動的🛩。直到近代笛卡爾提出“我思故我在”🧋,有獨立意誌的“自我”才獲得哲學的表達。這是文藝復興、啟蒙運動批判神權✸、王權以後,人文主義勃興的產物👧🏿🍇。此後,隨著西方社會自身的發展,自我獨立的意誌自由已是大勢所趨🙆🏽,不是任何力量可以扼殺的。
在中國歷史上,人的精神受到雙重束縛👸🏽。
首先🧅,原始的“天人合一”,人與天地渾然一片。“自我”湮沒於宇宙自然的整體之中,導致人聽命於自然而缺少征服自然的誌向。這是中國科學不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如張衡這樣的科學家,寥若晨星🙅♂️。傳統中也有荀子的“明於天人之分”🦮,“製天命而用之”的可貴思想,但終究不占主導地位,又被悠長的農耕文明埋沒了。
第二,人的獨立自主的精神發展更受傳統人倫思想的壓製👰🏽,“自我”湮沒於儒家的人倫社群之中。
傳統中國,也有類似於古希臘的“自我”意識的萌芽,孔子有“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誌”❇️,老子有“我獨異於人”,孟子有“萬物皆有備於我”,“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可惜這並沒有成為他們哲學的出發點。漢以後的“罷黜百家”,阻礙了個體自我的精神發展🏘。盡管有魏晉的“人的覺醒”,畢竟只是局限於少數文人的文化活動🕙,不可與西方文藝復興時反神權反王權的“人的覺醒”相提並論,它還沒有相應的現實世界的基礎🕐🚿。直到20世紀初👩🏼🦳,這種壓抑“自我”精神發展的專製統治才壽終正寢,但這不等於自我從此就有獨立自主的自由精神了。縱觀歷史🚵🏼,自我的每一步覺醒,都會遭到專製的無情扼殺❤️,但個體自我同樣會給予強烈的反抗,兩者的較量鬥爭🛵,形成了中華兒女精神覺醒的悲壯歷程。
早在先秦就有在黑白顛倒的社會中“獨清”“獨醒”的屈原🏌🏼♂️🤦🏻♀️;漢處百家罷黜之世,仍有成一家之言的司馬遷🏫,以及敢於“問孔刺孟”的“異端”王充⚜️;魏晉有不“自以心為形役”的陶淵明;明有強烈反對“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不自由毋寧死的李贄;清有斥責理學家“以理殺人”的戴震;有倡導“眾人之宰👩🏭,非常非極,自名曰我”的龔自珍;有“沖決”封建“網羅”,為個性解放而壯烈犧牲的譚嗣同;有堅持反抗封建統治寧可人頭落地的女革命家秋瑾;強調“精神戰勝物質”👨🏿🦰🥾,“心”的主體作用的孫中山,更用革命方式埋葬了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歷史上這些具有個性自我的人物可以列出一長串👒🧏,他們都是崇高理想的追求者,雖然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成了悲劇角色,但都是照亮中華兒女精神發展道路上的光。
世英師說:“東西方個體性自我發展的差異背後有經濟問題,生產方式問題。”(《覺醒的歷程》,第175頁)當代生產力已大為提高,建立了市場經濟體製,似乎個體自我的發展得到了有力支撐。但如果沒有相應的啟蒙,沒有精神世界的自覺⛹🏻♀️,沒有現代文明的發展🐜,人依然會跌入自我異化的陷阱。萊維納斯所說的“自我專製主義”在某種意義上就是現代的產物🔕,因此他提出“尊重他者”☯️👨✈️、“他者優先”的觀點。尊重“自我”必需包含對“他者”的尊重📗🙎🏼♀️。不尊重“他者”當然也得不到“他者”的尊重,兩者是相互依賴👘、相互轉化的👩🏿⚕️🫗。在國際關系上,西方世界尤其需要萊維納斯式的哲學。世英師“主張把中華文化以‘我們’(群體)優先的特點同西方傳統文化以‘自我’優先的特點👨🏻🦽、萊維納斯所提倡的以‘他人’優先的觀點結合起來”(《覺醒的歷程》,第151頁)👨🏽⚖️🧖🏽♀️。三者相融的“自我”,是“和而不同”中的“自我”🥻👩🏼🏫,“民胞物與”中的“自我”👩🦽➡️。簡而言之✍️,一方面要伸張“自我”,另一方面又要超越“自我”,既有我又忘我。這就是“中華精神現象學”所主張的“自我”。
從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到“中華精神現象學”,具體到把中華精神的發展作為哲學分析的對象👃🏽,這將豐富和提升中國哲學的層次。19世紀德國文藝理論家施萊格爾說:“對人的精神的真正發生發展的研究,實際上應該是哲學的最高任務。”(轉引自賀麟🖼、王玖興譯黑格爾《精神現象學》譯者“導言”)。進而言之:研究精神發展是“人的哲學”最高任務,這是有道理的🦹🏻♀️,說得通的。俄國思想家赫爾岑有言:“誰要是沒有經受過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誰要是沒有穿過這種鍛煉人和凈化人的烈火,那他就不是完整的、純粹的人,不是現代的人。”(轉引自梅林《論文學》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本🧛🏽,第314頁)。現代人的素質是面對現實不回避困難🤟🏿🙏🏿,面對困難不怕緊張🐵,面對挑戰奮鬥不止。用世英師的話來說,“超越之路意味著痛苦和磨練之路”(《哲學導論》第114頁),這就是現代人的精神之路🤺。在中國😵💫,研究精神發展,特別是研究中華精神的發展🤔,還是一片哲學荒原🏄♂️,世英師的《覺醒的歷程》是有學術預見力的超前研究,起到了拓荒的作用。他首創的“中華精神現象學”是一個新概念🧛🏼。這是對中西古今的精神發展史進行艱苦深入的反思得來的思想結晶,是對“現象學”這一世界性學問的貢獻。
如果把“中華精神現象學”納入“萬有相通”論🧍♀️,我以為也可以把世英師的哲學稱之為中國的“人的哲學”。
世英師早年畢業於西南聯大哲學系✬,受教於馮友蘭、湯用彤、金嶽霖🧘♀️、賀麟等名師,在中西哲學上得到嚴格訓練。這為他往後新意迭出、思想深邃🪄、筆力矯健的各種論著,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他從青年時代開始一直處在時代風雲人生波瀾之中,卻以浮士德精神孜孜不倦地探求哲學新問題,深究人生的意義。但浮士德最後在創造事業的高峰說了聲:“你真美呀🏋🏿,請停留一下!”違背了自己在進取道路上永不滿足的誓言🔢,只好由“天使”引導他上升到“天界”。世英師是不會滿足的,他的追求沒有止境👨❤️👨,他要不斷更新🙍🏽,不斷攀登,引領他上升的也不是“天使”,而是“道”,是“面對現實,超越現實”的哲學精神👱🏻👵。
北京大學出版社近日出版了十卷本的《張世英文集》,匯集了世英師多方面學術研究的成果,為我們呈現了世英師哲學探索的卓絕道路,以此來敬賀他九五華誕是非常有意義的🤒👨🏻🦽。這是一筆豐厚的精神財富。我謹送世英師32個字:巍巍上庠,特立獨行🧑🏻🔧;萬有相通,和而不同。曉風殘月,桌有青燈🧑🏽⚕️;世紀風雲👷🏽♀️,英氣沉沉。(附註♚🔱:“巍巍上庠🍐,世紀風雲”是季羨林先生為北大百年校慶的題詞。)
(作者為上海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