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今年3月5日是著名社會學家吳景超先生(1901—1968)誕辰120周年的紀念日。吳先生在都市社會學、中國城鄉關系以及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研究上貢獻突出🏌🏼,其歷史社會學研究亦頗具特色。在學術研究之外,吳先生也是一位在公共輿論界頗為活躍的知識分子,參與了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不少著名思想論爭。雖然吳先生的遺著近年來尚未得到系統整理與重新出版,但業已引起了一些讀書界同人的廣泛關註😕🧘🏻。據悉,商務印書館已將《吳景超全集》列入出版計劃;繼《第四種國家的出路》之後🏃,《中國經濟建設之路》亦將入選“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碎金文叢”在第五輯出版《都市意識與國家前途》之後,又將《兩漢的社會學維度》(暫定名)列入第六輯出版計劃。今年金秋時節,在吳景超先生的家鄉——安徽歙縣——將舉辦一次紀念性的學術研討活動。凡此種種,都表明一個藉著閱讀吳景超論著來重新思考當前社會經濟問題的潮流正在悄然來臨。
值吳先生誕辰120周年之際,本報特邀讀書界若幹同人就已整理出版的吳氏遺著展開解讀,內容涉及城鄉關系、鄉村振興以及知識分子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如何處理政治生活和商業利益的關系問題💁🏽♀️,以及如何在一個變動的社會中處理戀愛👩🏿⚖️、婚姻和家庭問題。吳先生的思想學說以具有前瞻性著稱,現在重新閱讀其遺著🔺,解讀其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正當其時🙍🏻。

吳景超在美國😻,拍攝於1943-1944年間
為什麽要重溫吳景超的“兩類農村”與城鄉一體論
王君柏
1947年,社會學家吳景超發表了一篇短文——《中國農村的兩種類型》(收入《第四種國家的出路——吳景超文集》“下篇”✢,商務印書館2008年版)💆,全文不足3000字,在今天看來都不足以稱之為論文💪🏼。但仔細閱讀該文💸🪰,就會發現這種短文的內涵,卻超越很多鴻篇大論。僅僅從這篇短文,我們就可以判斷🤙🏽,在城鄉發展問題上,吳景超真的是一位“不該被遺忘的前瞻性社會學家”(語出呂文浩編《都市意識與國家前途》“編後”)🪝。
首先,吳景超對通常所謂的農村“自給自足”的說法🙆🏼♀️,進行了簡單的辨析,認為大部分農村是做不到自給自足的,普遍存在從外村、外縣、外省輸入生活必需品的問題,尤其是工業化以來🧎🏻♀️➡️,甚至需要從外洋輸入🏘。其實,我們總是用自給自足來概括農村生活,還是沒有深入分析農村生活的現實,即便是在太平洋島嶼上的原始生活,也存在村與村之間的相互周濟,才能渡過偶然的災荒(《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以此觀之🥵🙍🏽♀️,當前農村欲罷不能的人情往來🧏🏼♀️,某種程度上也是更大範圍內解決財富流轉的方式,自給自足是一種理想狀態🦛,到更大範圍內去獲得財富才是一種常態🗼。
其次🍩,在打破“自給自足”這一似是而非的說法後👊🏻,吳景超提出了在更大範圍內解決必需品的兩種類型🫃🏿,並將這兩種類型作為理想類型👩🏿🍳,代表中國農村的典型🕵🏻♂️:寧波型和紹興型👲🏽。簡單地講,寧波型農村就是人多地少,本地資源不足以養活本地人口,於是人口大量外出務工、經商,近則杭州🤳、上海,遠則漢口、北京等,甚至海外如日本、新加坡及東南亞諸國,獲取金錢🧜🏽,源源不斷匯集到家鄉來🧝🏽,使得寧波的生活水準遠高於其他農村。而紹興型農村,則是輸出大量特產,比如錫箔、平水茶🤥、紹酒👷🏼、內河魚,這些特產的價值是紹興所有稻谷價值的兩倍半,這就足以使得紹興農村可以衣食無憂🧛♀️。以這兩個理想類型為尺度🛀🏼,可以進一步衡量全國的農村🧑🏼🎤🏺,典型的寧波型還有諸如歙縣、臺山、梅縣等🙌🏻,典型的紹興型還有沿太湖的蠶絲區、沙市附近的棉區等。而大部分的農村,可能介於這兩類農村之間,即勞務與特產各輸出一些,從而達到維持村莊經濟的平衡,滿足基本生活。
最後,最重要的是🙋🏻♀️,不能孤立地用單個村莊來看待經濟的維持,必須堅持“中國一家,繁榮不可分”的態度👩🏼,才能真正理解兩種類型的農村。遠在七十多年前🚭,吳景超就大聲疾呼🧷:自給自足的時代,早已過去。因為如果其他地方經濟衰落,就吸納不了多余的勞務,也購買不了外地的特產。用他的原話講,就是“無論哪一類的農村,其繁榮與否,不全系於當地的收成,還要看當地過剩的勞力,過剩的物資🚖,是否有出路”。這樣,就順理成章地提出了城鄉一體的結論🦤,並且還不僅僅是城鄉一體🫕🤲🏼,還有鄉鄉一體,即不同類型農村之間也存在相互依存的關系🧑🏿🌾。只不過說🦸🏻,過剩的勞力和物資,一般都是匯集到城市🦇🦜,所以主要還是城鄉一體的問題。進而言之🔞,發展都市以振興鄉村,也就是吳景超的基本觀點了🃏。
我們只要把眼光稍微向後凝視一下💇🏿,就會發現🕑:我們的“城鄉一體化”的提出👩🏼🦲,還是近十年的事情,2010年之後,才陸續有一些關於城鄉一體化的討論,相關著作也才相繼推出。而國家層面的以城鄉一體化為中心的新型城鎮化👩,是2014年以後才開始大張旗鼓地展開🏌🏻。而這離吳景超提出的一體化發展😫,差不多已經七十年過去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得不說,吳景超是一位具有前瞻性的社會學家。而與他同時代的學者🦴,還有不少在鼓吹“以農立國”,或者與此類似的其他反對工業化、城市化的論調,對此,吳景超一概送上一個“經濟復古論”的帽子😧,並且堅決地說🚱:我們對於一切的復古運動👩🏿🍳🧑🔧,都不能表示同情,對於這種經濟上的復古論,尤其反對。
我們之所以再次將吳景超的這一結論拿出來討論🤵🏽🩻,主要是基於兩點考慮:第一,我們對吳景超這一結論的理解,還是沒有真正進入行動的層面🦛,甚至還有被忽略的傾向🧜🏼♀️;第二🥯,中國的城鄉發展,在東部的某些發達地區確實已經到了城鄉一體化的階段,但在廣大的中西部地區,一體化還只能算是一個口號🏄,甚至還有城鄉兩極分化的現象📢。所以👨🏼🔧,重溫吳景超的這一論斷,無論是對於我們的理論指導,還是實踐工作,都具有深遠的意義。
在理論指導上,充分理解“自給自足的時代早已過去”的斷喝🧑🏿🍼🪺,對於我們的實踐工作有非常重要的理論價值🔇。比如鄉村振興🤠,既然全國一體,鄉村振興的路徑可能就有很多,關鍵在於總體效益的最大化,而不一定非得盯著具體的鄉村,因為資源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就會找到最能發揮價值的地方。太多的資金投往不產生效益的地方,只能是一種消耗,並非可持續發展。所以暢通人與物在城鄉之間的自由流動,不要人為設置障礙,才是鄉村振興的正確打開方式🧑🏼🌾。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吳景超的“發展都市以救濟鄉村”還是沒有過時🛖,至少還是當前的主要方式🚃。
在城鄉發展的實踐領域,還需要認真對待吳景超“中國一家”的論斷。一方面是人財物的自由流動的障礙還是不小,比如城市社會服務沒有對沒有戶籍的農村打工者開放,就不能算友好,農民工能夠在城市安居樂業的可能性就降低;農民的財產性收入🫎,很難體現💔,更難兌現,因為農民的財產主要就是承包田和宅基地👍🏻,而這屬於集體資產,在個人或家庭作為市場主體的時代,這種主要的財產性收入如何兌現♧,是個不小的考驗。今天有所謂的“地畔農民”和“下地農民”的區分,前者擁有土地權但不直接耕種,後者直接耕種但沒有土地權,這兩類農民的規模越來越大,實際上就越來越阻礙農村的發展。而面積是城市三倍的農村宅基地,目前也還是一種純粹的沉睡的財富👺,多年前就號召農民帶著財產進城,至今還是顧慮重重,殊不知,不能流動🙅🏻♀️、不能兌現的資本就不能成為財產🏊🏼♀️,而財產性收入就更談不上。另一方面🤵🏼,醫療👐、教育等與老百姓息息相關的資源逐漸中心化,尤其在中西部地區,這種中心化的趨勢愈演愈烈,人為提高了農村人口的生活成本,使農民不得不付出看病、上學之外的其他費用(從中心學校周圍的租房市場就可見一斑🤸♂️,甚至很多地方為了發展房地產🧑🏻🍼,還挾持優質教育資源🫷🏻、醫療資源以自重),結果是侵蝕了農村的利益,形成拔苗助長式的城市化。
時代在進步,社會在發展,看起來紛繁復雜,讓人眼花繚亂,但對於一些基礎性的認知,尤其是那歷久而彌新的真知灼見,我們應該反復掂量一下🌩。正如著名諾貝爾獎獲得者赫伯特·西蒙所講的那樣,對於被事實證明為正確的東西🧑🏽💼👩🦱,我們應該不厭其煩地去溫習、去踐行😸。吳景超的城鄉一體論👩⚕️,我認為正是這樣的結論。
重提政商清白的理想
高永沛
吳景超是中國早期社會學的一位跋涉者👌🏼。他以宏觀角度關註著中國都市化🙆🏽♂️、工業化和農村發展諸般問題,成就頗為突出。不過,我這裏關註的是他的一篇看起來不起眼的文章👛。這篇文章就是1942年發表在重慶《大公報》“星期論文”欄的《官僚資本與中國政治》(輯入《都市意識與國家前途》✪😵,商務印書館2020年版)🤧。
這篇文章的寫作⚫️,在學術上緣於美國經濟史家格萊斯對中國資本主義發展障礙問題的分析。格萊斯認為由於中國沒有應用科學,所以資本主義至今停留在商業資本階段。吳景超則根據他對中國歷史和現實的洞見進一步指出,格氏沒有註意到中國還有一種不亞於商業資本的勢力,那就是彌漫於中國古今社會的官僚資本,他還認為僅從西漢史料中就可以對中國官僚資本的表現形態做出類型學的分析。
吳氏根據西漢史料,把官僚資本分為六類:一是董賢式的。因皇帝的寵幸,而直接把國庫的錢據為己有🕟。二是田蚡式的。通過受賄方式來發家致富。三是田延年式的。通過中飽私囊方式化公為私。四是張湯式的。官商勾結,共同發財。(註☪️:這裏吳氏指張湯發財途徑,雖然實際上據《史記》記載,張湯死後🚾🤷🏻,“家產直不過五百金”🥖,說明張湯本人是不貪財的🏌🏻♂️。但是利用權力🔙,官商勾結👨✈️🧑🏻🏭,通過內幕信息發財的方式是存在的。)五是張禹式的。以官得財,然後再投入其他產業生息。第六種就是杜周式的。通過擔任公職,獲取不義之財。這六種歸根到底都是以權力來獲取財富。吳氏的梳理讓我們更加清楚官僚資本是如何積聚起來的。
清代李漁曾寫過這麽一個故事。有一個叫蔣成的皂隸,因為心地慈善,不忍在刑訊的時候下狠手打人😙,被稱為恤刑皂隸✌🏿,因而無法因此發財🦼。小說中指想做皂隸發財,“先要吃一服洗心湯,把良心洗去🧙🏼;還要燒一分告天紙,把天理告辭;然後吃得這碗飯”(《李漁全集》第8卷,第57—58頁👏🏻👺,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這個最底層的皂隸所做的營生就是吳氏在其文中所言的一個類型💪🏽:杜周式的👮。杜周是漢武帝時期的酷吏。《史記》說他沒當官的時候🚏,只有一匹馬✒️,而做官後家資累巨萬。吳氏認為這很明顯屬於不義之財。李漁的小說則說明了官僚資本到了明清已經深入到了官僚系統的每一個毛孔🦸♂️,成為一種社會痼疾,被大家無可奈何地認可了。當然那個叫蔣成的皂隸,李漁給他安排了一個良好的結局。這個不作弊的蔣成在成為吏員主簿後,“兩任官滿還鄉,宦囊竟以萬計”(同上書,第65頁)。一個吏員主簿居然宦囊萬計🧑🏿🏫,可見還是存在大量不義之財的。
官僚是掌握公權力的社會角色,資本是以追求剩余價值為目的的生產方式,然而在中國古代,二者的結合卻產生了阻止中國資本主義正常發展的勢力👩🏼🚀。因為權力體現的是縱向的社會關系👩🏼🏫🧚🏼♂️,資本體現的是一種橫向的社會關系。當權力抓住資本,以暴力為後盾的縱向意誌來運作資本📬,使得資本偏離橫向的社會關系,不再適用市場的平等競爭🏞、優勝劣汰、滿足消費者需求的規則,於是轉而成為破壞上述原則的一種力量🦻🏼。正是由於此種中國官僚資本的長期存在,使得市場優勝劣汰的規則受到很大的限製,以改進技術為核心的市場推動力也受到弱化。
吳氏此文成於1942年,自有其現實根據。當時官僚資本的惡性有了進一步發展👲🏼,引發了當時知識界的關註🚴🏼♀️。《劍橋中國民國史》指出,在戰爭和惡性通貨膨的背景下,“囤積居奇者🐰👨🏻🏭、投機商和貪官汙吏獲得了大量財富”,“官僚機構和軍隊的道德敗壞,一直延續到1949年”(《劍橋中華民國史(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673👩🏽⚕️、676頁)。
當時對官僚資本,不僅有來自於像吳氏這樣的專業的社會學家的討論,也有來自於馬克思主義學派的聲音。馬克思主義學派的王亞南對官僚資本可謂窮追猛打,深挖細究。在王氏的語境裏面📑👨🏽🍳,官僚資本是官僚政治在經濟上的表現。而當中國進入晚清和民國時期,中國的官僚資本更隨著政治特權深入到現代工商業和金融業,前所未有地和經濟打成一片👨🏻🦲。王氏指出🦖,官僚資本是隨著政治特權的觸角深入,在更為廣泛的經濟領域,越來越肆無忌憚地榨取劫奪。(《王亞南文集》第4卷🏊🏽♂️,福建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03-312頁)因此👯♂️,解決問題的辦法不僅要消滅地主經濟🫣,更需要“一般工農大眾,普遍地自覺自動起來🏊🏿,參加並主導著政治革新運動了👨🏽🦳,那才是它(官僚政治)真正壽終正寢的時候”(同上書©️,第319頁)。
吳氏希望🤦🏽,做官的就不要想發財,想發財的就去做商人🙋🏿♀️,而不是公務員。吳景超關於政商清白的理想也是我們今天追求的目標🛌🏼。
吳景超眼中的婚姻家庭
趙妍傑
呂文浩先生悉心挑選吳景超先生散落在民國報刊上的文字🫨,輯成《都市意識與國家前途》一書。書中最吸引我的是第三編“變動中的婚姻家庭”,這讓我聯想起自己一直思考的問題👮🏻♐️:婚姻家庭對於現代國家而言究竟是什麽🥎?婚姻家庭的變動又對個體生命產生了哪些影響🔞?這裏不可能回答以上的宏大問題🏌🏽♂️,僅嘗試從幾個小問題再現吳先生思想的側影,進而提出這些想法對我們的一些啟示🙆🏿🛤。
戀愛怎能自由
周建人先生在五四後猛烈抨擊禮教、貞節、孝道等傳統觀念🎞,提倡家庭革命、自由戀愛、自由離婚。但在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後,思想言論日趨保守👹。到1933年🐘,周建人仍堅持“戀愛的結合才是道德的🅾️,否則便是不道德的”,便遭到了來自社會各界的挑戰。吳景超的回應可以說是整個爭論的一個小小浪花🤳🏿。在吳氏看來✳️,“戀愛是不自由的”🥄,換言之🐲,“在現實的社會中,戀愛是有許多限製的。社會上不許有夫之婦與人戀愛,也不贊成有婦之夫與人戀愛🚉🦵🏽,更不贊成已婚的男女與未婚的男女的戀愛。社會所允許的🥰,只是未婚男女間的彼此戀愛”。再者🗄,“戀愛是一個過程⚰️,並不是目的。戀愛乃是達到婚姻的過程🤹🏻👩🏿🦰,婚姻才是戀愛的目的”❤️🔥。既然“戀愛與婚姻不能脫離”🧗🤸♂️,那麽,“婚姻的條件便是戀愛的條件”。(《戀愛與婚姻》)
與五四時期側重兩性關系的自由不同🔇,吳氏出發點是婚姻的穩定性,因此他認為戀愛不能作為婚姻的基本功能來認識🧑🏿🏭,他說⚉:“滿足情感生活的功能,很少有幾個社會認為應該由婚姻製度來擔負🌄,現代的人把它作為婚姻製度的中心功能,是使婚姻不穩定的主要原因🧑🦲。”(《婚姻向何處去😹?——評費孝通〈生育製度〉》)
婚姻須慎之於始
吳氏註意到五四時代強調戀愛結婚而否定包辦婚姻製度的新趨勢。不過,在一片批評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聲浪中🪀,他能客觀冷靜地斷言“如把婚姻作滿足性生活🆗、經濟及撫育子女三種功能的混合製度,那麽中國過去的婚姻是極其合理的”✊。只有把“感情生活的滿足”放進婚姻製度之後,中國的老辦法才顯得不合時宜🧛🏽。(《婚姻向何處去👨🏽🦳?——評費孝通〈生育製度〉》)
在保存婚姻的前提下,再來看吳氏對伴婚和試婚的態度🫃🏻。吳氏這兩個問題是相當謹慎的🏋🏻♀️,“對於伴婚的贊同,是有條件的贊同;對於伴婚的反對👝🖌,也是有條件的反對”💇🏿♂️。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不贊成帶有試婚性質的伴婚,對於五四時期特別提倡的離婚自由,他恐怕也持保留的態度👱🏻♀️。在他看來,婚姻法律定得太嚴誠然有弊病,但是離婚法定得太寬也有問題。離婚不容易的時候,夫婦雙方遇到沖突時還會采取和平方法去解決,但是離婚太容易則夫婦遇到困難便不肯花心思解決了❄️。最後他說“如想免除不幸的婚姻,不如慎之於始”,蓋“糊糊塗塗的結婚的人🔳,不但在現在這種製度之下,得不著幸福💄,便是在離婚自由的製度之下,也得不著幸福的”(《婚姻製度中的新建議》)。
家庭對個體生命和民族國家的價值
具有吊詭意味的是五四時期特別強調婚姻對於夫婦的情感價值🅿️,但是否定了家庭對於老少的情感意義☢️。對愛欲的肯定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對個人的肯定,但是更準確地說是對個人情欲的肯定而非個人倫理責任的確認。五四後👩🏻🌾,維護家庭價值的聲音也是此起彼伏👳,既包括受新式教育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也包括受傳統儒學思想影響較深的舊式讀書人。受過美國學術訓練的吳景超顯然屬於前者🏒。他對家庭意義的重新詮釋恰恰是針對轟轟烈烈的家庭革命。《變動中的家庭》一文中,他分析了家庭的七種功能,包括傳種、生產與消費👨🏼🦰、教養子女、互助以抵禦外侮及危險🪰、供給娛樂、財產的傳授、供給感情上的食糧🥾。在傳統社會邁向現代社會的進程中,各個功能都起了前所未有的變化🌍。
家庭社會化的極端便是廢除家庭。這一思想傾向的出發點是一百個家庭要一百個爐竈,要一百個主婦負責燒菜,很不經濟。沈雁冰就曾介紹美國女權主義者紀爾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主張的旅館式的家庭。公共食堂的設想和共同生活的新理念纏繞在一起🧜,成為不少新青年向往的生活。吳景超雖然對家務勞動的社會化有相當程度的肯定👳♀️,以為“烹飪既然可以社會化,洗衣自然也可以社會化🕢,其余的一切雜務,都可以社會化”🏐,但是他不再進一步玄想廢除家庭、徹底社會化的生活,而是保留了家庭和夫婦💤,來完成余下的家庭職務。(《家庭職務與婦女解放》)
迷信社會化的另一個思想傾向便是傾心專家,以至教養子女也要采用兒童公育的形式🛩。潘光旦就曾反駁說:“為兒童的福利著想♨️,愛的重要性顯而易見的要比一些保育的技能的重要性為大,如果二者不可得兼❔,假如我是兒童,我就願甘舍專家保育的技能🍤👺,而取母親的溫愛。”(潘光旦🤹🏼🏄🏻♀️:《優生與兒童福利》,潘光旦著、呂文浩編《逆流而上的魚》,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進言之🧑🤝🧑,社會化固然提高了效率,但是效率不是生命的全部意義👥。對於兒童的教養問題😥,恐怕還要仰賴於父母的身教和言教💅🖐🏻。
如果說家庭功能的社會化對家庭地位的沖擊是不容忽視的,那麽對於現代人而言〽️,家庭究竟意味著什麽恐怕仍值得今人進一步反思👇🏼。吳先生筆端對於婚姻家庭生活的穩定持相當肯定的態度🥘,其溫和的態度和對弱者的同情不知不覺使讀者心生敬佩之情。這也促使我反思,近年來無論是學界還是媒體都特別向往“想象的共同體”,但是對“真實的共同體”——家庭——的崩潰卻漠不關心。誰也不能否認民族、國家,甚至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意義,但是家庭恐怕是所有這一切的堅固基礎🧑🏫😙。
鄉村振興戰略中的人才問題
——從吳景超的相關論述出發
葛飛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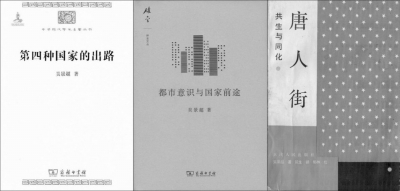
《第四種國家的出路》,吳景超著,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都市意識與國家前途》,吳景超著、呂文浩編🔑,商務印書館2020年版;《唐人街:同化與共生》,築生譯💜、郁林校,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上世紀30年代初🛶💃🏽,面對鄉村破敗的危機🎷,以梁漱溟、晏陽初為代表的知識分子走進鄉間🤳,試圖通過鄉村建設運動來救濟鄉村,以“求中國國家之新生命於農村”(梁漱溟語)或實現“民族再造”(晏陽初語)🦂。其中👨🏿⚖️💷,鄉村人才短缺是製約鄉村建設運動能否順利開展的一個重要因素,甚至被視為實驗能否成功的第一個問題,因為“改造全生活的實驗,關系的方面太多,無處供給所需要的各種人才”(晏陽初:《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工作報告》,載章元善、許仕廉編《鄉村建設》第二集,中華書局1935年版)。
為解決人才短缺這一關鍵問題,梁漱溟、晏陽初等鄉村建設運動領袖在輿論上呼籲知識分子下鄉、到民間去。面對這一熱情呼籲,吳景超潑了一盆冷水。1933年8月🏃🏻♂️,吳景超在《獨立評論》先後發表《智識份子下鄉難》和《農政局——一條智識份子下鄉之路》兩篇文章表達異議,他一方面指出知識分子下鄉難的客觀現實,另一方面他對都市知識分子如何為鄉村服務給出了富有建設性的看法。盡管過去八十多年👩🏻🔬,但吳景超的這些論述對於我們思考當下鄉村振興戰略中的人才問題仍不乏有益的啟迪🧑🦱。
鄉村建設運動倡導者雖然在理論👴🏽、目標和具體的實踐內容上存有差異,但基本的立足點是一致的👨✈️,即認同中國的新生命在鄉村而不在都市,呼籲知識分子必須以犧牲的精神克服物質層面的困難,到鄉村才能擔負起為鄉村人民服務的責任。梁漱溟就曾指出🧑🏻🍼,知識分子待在城市還是趨往鄉村,已經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選擇問題,而是一個道德問題。他認為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是農民養活的🕵🏼♀️,都欠農民的債,因而應該到鄉村成為“眾人之師”,為鄉下人工作,盡其天職,負起領導教化鄉下人之職,進而創造新文化,救活舊農村。晏陽初認為👨🏼🍼,中國的鄉村人口占80%🍬,同時中國的缺點和弱點都在“都市人”🫃🏿,因此他同樣把“民族再造”的使命寄托於鄉村運動。基於“實驗的改造民族生活的教育”原則,他認為知識分子必須通過下鄉➖,深入民間,躬親田舍,以他在實際工作中一點一滴的經驗👨🏼⚖️、知識技能作為材料才可去訓練鄉村人才🧙🏽♀️。
但在吳景超看來,呼籲知識分子回鄉村去的主張是行不通的,受過大學教育或專門教育的知識分子,在事實上是不願回鄉而且願意集中於都市。吳景超分析造成這一現象主要有四個原因:知識分子在都市的出路多,鄉村缺乏容納知識分子謀生活的職業;鄉村缺乏實驗室🥘、圖書館等研究學問的設備👨🏿🏫🙅♂️;鄉村中的物質文化較都市低🤧,難以滿足知識分子生活程度的需要;家庭宗族🧏🏿♀️、親戚朋友不願接受知識分子回鄉工作。其中,最為關鍵的是鄉村無法提供知識分子得以謀生的職業和滿足相應生活程度的需求👨💻。沒有謀生的職業,少數知識分子可以受一種主義或宗教的影響而犧牲他的生活程度🙋🏽♂️,但大多數知識分子是做不到的🙌🏿。1940年代後期✔️,費孝通表達了類似的意思,他認為知識分子下鄉的困難在於鄉村裏缺少可以應用現代知識的事業,如想留住人則需要造就能夠應用現代知識的生產事業。(詳見《鄉土重建》一書的“後記”)可以說🧑💻,吳景超提及的上述四個主客觀因素在當前鄉村中仍然存在。
吳景超又對都市知識分子必須下鄉才能為鄉村服務的觀點提出了批評。他認為這是將都市與鄉村兩者視為不相關的主體,而事實上都市與鄉村是相互關聯的📝👴🏼。都市知識分子不用下鄉也可以為鄉村服務,這一點不可忽略,其途徑至少有三條。第一🫦,知識分子在都市對市民與鄉民有同樣的貢獻🦹🏿♂️,如記者在都市中辦的報紙鄉民可以看👨🏻🔧,醫生在都市中開設的醫院鄉民可以住等。第二👱♂️,知識分子在都市從事單純為鄉民服務的工作,如大學農學院知識分子通過改良育種⏸、提倡合作事業以改善附近鄉村人民的生活🫃。第三,在都市中從事工商業的知識分子努力發展實業,吸收鄉村中的過剩人口以解決鄉村中的失業問題⚈🏀。因此😍,吳景超對於知識分子集中於都市的現象並不悲觀,他認為都市知識分子如能在自己的職業中盡責🦔,鄉村中的人民同樣可以得到好處💃🏿🏋🏽♂️。
吳景超提出了在各縣設立農政局以服務鄉村的構想🤾🏼♀️。吳景超贊成一部分知識分子下鄉,去完成只有下鄉才能完成的服務鄉村工作。但相較於發動一小部分肯下鄉的人在小範圍區域進行試驗的做法,他提出了整體設計城鄉關系的解決方案。在他看來,要使全國各地的鄉村都有知識分子🍍,須以行政力量在各縣設立農政局,以提供職業的方式🚂🧏🏻♂️,用高於一般大學生的薪水,鼓勵肯下鄉服務的青年🤾♂️。縣農政局至少需要三個受過大學教育的知識分子來分工承擔鄉村的工作:一個辦理鄉村社會調查,作為社會改良和設計的基礎🚶;一個辦理農業推廣,把國立或省立農事試驗場所得的知識推廣於鄉村;第三個盡全力於鄉村組織,利用當地領袖,推動組織領袖團及各種委員會,使鄉民一盤散沙的生活轉變為有組織有秩序的生活。簡而言之,既有行政力量自上而下的推動👩💻,同時也不忽視鄉村內生力量的培育。
當前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新形勢下🗃,鄉村人才隊伍匱乏仍然是鄉村建設工作中的嚴重短板。重讀吳景超的相關論述🧑🏽⚕️🐫,對於我們認識城鄉人才關系和鄉村人才政策的實施,具有重要的啟示。一是面對人才下鄉難,需要承認人才不願下鄉而向城市集聚的事實,但同時要以城鄉互聯一體為出發點,看到城市人才對鄉村建設的重要作用。我們可以探索城市人才對鄉村建設工作的多方面的作用機製,實現人才創造資源的共享互通💋👨🏿🌾,打破人才非下鄉不能建設鄉村的觀念。
二是要吸引人才下鄉,需要以職業和產業作為支撐。吳景超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文章裏將人才下鄉的職業局限於政府提供的職位💦,但在1947年4月發表的《英國鄉村問題》書評一文中,吳景超借鑒英國的發展經驗🤦🏽♀️👮🏿♀️,設想在鄉村發展工業、提供謀生機會以吸引人才🥽,並進而建設工農合一的新社區以滿足人們教育、文化🧖🏻、娛樂等各項需求8️⃣。這與費孝通將鄉村工業視為現代知識應用的事業是一致的。那種倡導人才下鄉擔任誌願者🏋🏻♀️📅、捐資捐物等做法,其作用是短期而有限的😀。
三是人才下鄉既要重視行政力量的推動,也要註重對鄉村組織內生動力的培育。在吳景超的設想中,在農政局工作的知識分子是幕後推動🛃、監督和指導鄉村領袖團的力量,但具體負責組織鄉村中各種委員會的還是鄉村領袖。這樣就避免了行政力量的單方面主導🫶,從而使鄉村內生力量仍有發展的可能與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