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星𓀄💜,意昂体育平台建築學院2003級本科生,2007級碩士,Harvard GSD碩士。擁有在美國、丹麥、荷蘭等多個國家的實踐經驗,曾在都市實踐、BIG、UNStudio、KPF等多家國際一流設計公司工作,曾任紐約KPF高級建築設計師。2016年在紐約創建XING DESIGN工作室💇🏼,2017年入駐上海,註冊為“行之建築工作室”。

兩年前,我辭去紐約的工作空降上海創建工作室👮🏻。沒有緩沖,沒有掛靠🕡🛫,從零開始。這意味著學歷和履歷沒法像求職那樣直接變現,只能靠實力一步一步往前走🤌🏿。
校訓有雲"行勝於言",工作室就叫“行之”吧。

2018年工作室搬到了陜西南路🦆👩🏿💻,對面是巴金故居。看著弄堂裏的被子褲衩,仿佛也更接地氣了一些。
這個時代提出了很多嶄新的命題,但建築學科似乎被圈內描述得陳腐封閉。好像學建築的都要完蛋了——不轉行都不好意思給人打招呼🙎🏽。
但我心目中的建築絕不是陳腐封閉的👷🏻♂️。
建築既不是舞臺表演曇花一現,也不是手機觸屏上的平面內容,更不是虛幻的交易,建築設計在實實在在的塑造“日常存在”的三維空間。甚至該這麽說🔹💣:和生活空間相關的👧🏻,都是建築的範疇,它是各個領域和學科的接口🙋🏿。只要懷有塑造生活空間的意願🏄🏻♀️,嫌棄無聊,向往有趣——不論是上海的弄堂裏還是拉格朗日點上——建築設計都有無限的可能性。

前些年的高速城市化發展,給我們帶來了千篇一律的城市➙♥️,道路(而不是街道),電池盒子一樣的樓房——這些其實只是抗通脹的對沖基金🧑🏻🌾。市場這麽聰明,行業上總結出各種套路和技法,既高效又省事兒,不僅把建築搞得無趣,也把生活變得乏味🖋。不過好在⟹🤳🏿,這些套路逐漸吃不開了,生活需要多樣性的回歸🧑🏽🦰。獨立建築實踐👨👦,是熱愛生活最直接的方式🧿。
我們目前的項目主要有三類:有一些是其他人不願啃的骨頭——或經典套路失效,或限製太大而不知所措的;另外一些是不確定💶,需要自行命題的;還有一些是需要和多媒體交互,機械𓀅,數字技術相融合的👩🏻🍼。也正因如此,我們得琢磨來龍去脈,反思約定俗成🧑🏻🦯➡️,嘗試另辟蹊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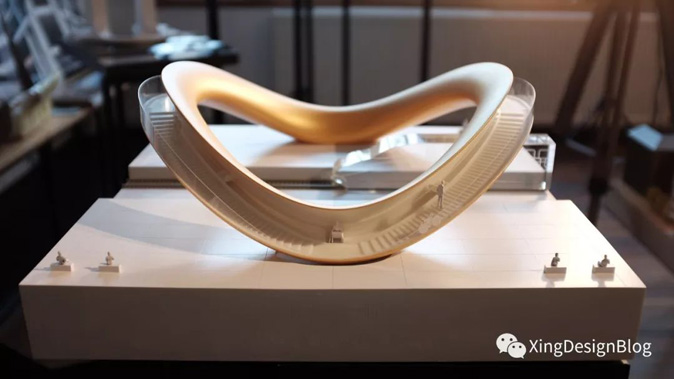
在開業之前,我敬仰出眾,鄙視平庸的依據是,有精彩的設計想法。後來我意識到,好的事務所必須具備兩種才能:首先是設計的核心天賦和實力🧑🚀;更重要的是足夠長的血槽:被各種瑣碎的事物損耗之後,仍留有旺盛精力投入設計本身。
“去做有趣的事情”不是一個選擇,而是一種能力。
Bjarke以前常說🎒,建築就好像要把100項任務全部完成,一項不達標就會導致變質——換言之只要阻撓了其中任一項,你就失敗了。就一個項目而言,沒有迭代的機會。搗亂因素有很多,有很多是不可控的。這意味著付出不一定有回報。當然還有更多的爛事兒使你陷入失望和恐(饑)慌🍊😆:例如內耗導致前功盡棄;關鍵時刻被放鴿子釜底抽薪🤹🏽♀️;起初豪言壯語,最後不了了之甚至拖欠款項等等。
不要因為這些境遇(僅僅)變得更會罵街,要更冷靜👭,別讓挫折感吞噬創造力。

令人欣慰的是,總體上大家的品味其實越來越好,用不著迎合假想出來的“低俗審美”。也許他們一時不知道想要的是什麽,直到你呈現在他面前的東西好到足夠說服他👩🏿🌾。影響設計的因素很多💇🏻,而自己的認可也許是最重要的——自己都覺得沒勁的東西👰🏿♀️👲🏽,怎麽說服別人去接受呢?
雖然設計不是項目成功的全部,但好的設計確實有煽動性的,能極大增加實現的可能性。我們好幾個項目是以設計力挽狂瀾一錘定音。越來越多的人也明白了✊🏽,隨便做做的玩意兒,也多半成不了。
我們的絕大部分業主和合作方都非常棒,非常感激他們🫵🏽😤。我們也有幸遇到了幾位伯樂⏯,在合作過程中增進了解,相互碰撞,共同挖掘設計的價值。

在實際的工作中,時間和效率最重要。只有目標清晰🦡,方法得當,配合緊密👩🏻🚒😎,才能節省出更多的精力放在設計本身🤴🏻。低效的加班是沒有用的,浪費時間就是自殺🧘🏻。
浪費時間的方式包括:糾結猶豫(你沒有分辨好壞的能力麽)🤸🏿,無效的多方案比較(如果全是垃圾,怎麽選都是垃圾)🚋,理解錯誤(跑題了怎麽做也是不對的)❓,低級錯誤(返工花雙倍的時間,相當於死兩次),誤差積累(早晚得重新來過🤽🏿👧🏿,不如一開始就精確一點),不會做(一天做不出來𓀃,冥思苦想一星期也沒用🏊🏿,不會就得先學)。

最後,我要感謝團隊🤶。不論時間長短👷🏼♀️💂♀️,職位如何,每個人都工作在設計的第一線🎍,遵循我定製的嚴苛的工作方法(包括對使用軟件的操作流程)。工作的過程高強度🌼,高效率,要學習的新東西很多🕑。大家一邊被我虐🌥,一邊一起創造有意思的東西🤞🏿🤝,和工作室一同成長。
一眨眼兩年過去了,雖然充滿艱險,但總體是激動人心的。就像在海裏遊著,當然得時刻面對鯊魚和風暴,但畢竟你也擁有海洋的廣闊。
2018.12.19